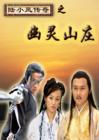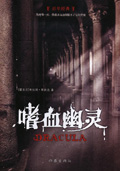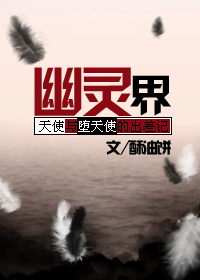��ɽ�����-��1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û�˽�ȥ��������ݷ����ˡ�
������ϸ������Ȼ�ڻ����Ӳ�����֮����Լ��һ����ɫ��ڡ�
����ת����ǰ����������ç֮�С��о�������һ��ֲ������һ�ŵ���ڴ�Ĺ֮�С�
������϶�����������ڣ��һڣǰ�IJ�����������һ��ʯ�����Ѷϳ����顣��һڣǰ��һ�ޱ����������ֻ��Ҳ�������ڵ�ס�ˡ�
�����Һ��������ҿ����ˣ���������б��������һ�£�
����ũ��ѭ��Ҳ���˽��������ﲻͣ��˵��ѽ���㵨������Ҵ������ҵ��������ġ�
�������յ����ԡ��ý�̤�������ۣ����ҷ����Ƿ�����ǰ��֦������ѹ��һ��֦�����µĸ����֦���ִ�����˷���б�˹�����
�������߰��������ϵ���ģ�����塣�����ƾ������������Ͽ��С��ü�ɽˮ�����֣���ϡ�ɱ档
���������߰ɣ�ũ�������뿪�������������ç��յ�ĹȦ��
������Ҫ���ˡ������Ķ��ӽ�ʲô���֣�������磿����ʲôʱ������ܰ���æ��
������һ���쳣�˷ܣ������չ����Ų������һ����ɽ��·������ǧ������ɣ���˵�������ء���˵����ô�ĸ��ڼ�û�������أ�
������������ģ�ũ������˵��û�˸����������ᆳ�����˿����л��߲���������������Ҳ�����ۿ����������ֱȻ��ɴִֵ�ˮͰ״˵������ô���أ��Ǵ������ߣ������ش���ǰ����ȥ���������µIJݶ�ѹƽ�ˡ���ָ�Ų�Զ�����������еİ�ʯ�ž�˵���Ǿ�ˮ�ɺ��ˣ���Ȼ��Ȫˮ����
����һֻ�ݹ�����ɽ�����ڲ����в�ȥ�������ָ�����������������ǰͷ������ȥ������ũ�������Ĺ���
����ũ���Ҿ��ڴ�ͷ��Դ�³ィ�����ı���Ժ��ˮ���̵أ�����һ�صľɲ���ƿ����Լ����������ҩˮ���ġ�һ���������ƽ�������κ�װ�ޣ�����˵�Ǽ�ͽ�ıڡ�ũ��������վ��Ժ�ſڣ��Ա�ͣ��һ��װ����С���֣������Ӳ��ߣ���ʮ��ͷ�����ӡ�ũ��Ҳ��������䡣
���������ó�һ�Ŷ��ӵ���Ƭ���ң�����˵��Ƭ�ϵĵ�λ�Ѳ��Ƕ������ڵĵ�λ�ˡ������������֣�������˵��˵�����ӵ����־Ϳ����ˡ�
������ʱ��Ů��ʹ�˸���ɫ�����ˣ����ҿ��������ý��Ҷ�����ɣ�
������֪������һ����ݴ���Ҷ��ԼҪ�Ѷ��ٹ���������������Ѯ�ɼ��Ĵ��裬�����ڴ�������֮�䣬��ʱ�IJ���ֻ¶�����ǵ�㼫ϸ��Сѿ�⣬��ժ7��8���ѿͷ�����Ƴ�һ�KƷ���ݴ�����������֮ǰ��ժ���׳ơ���ǰ�衱��ʮ�ֽ��һ��������ǰ��ÿ��Ҳ��Լ��6�����ҵ�ѿͷ�����������������������ij��࣬һ���ҶҲ����Ҫժ4��5���ѿͷ�����︶��������ɼ�һ�ߡ���æ��ǣ���˵��ϲ���Ȳ裬���ÿ������߿첽�߳���ȥ����ʱ���Ҽһ����������շ��ˡ�
������������壬�����DZ��ݷ��ɽ�룬�ڴ�ׯ��ͨ��ɽ�ŵĵ�·֮�䣬����һ������ĵ���أ����Ϸֲ��ܶ��ʯ��ũ��˵����ʯ��ɽ����һֻ������״��
��������㿴��һ�ۣ�����������ڣ�������ʲô��״��ֻ��������һ��������ب����Ȼ��ɫʯǽ����С���ڵ���Χ��������
����
����Ϧ���е�����ɽ���㻹�ܰ�����ã���1��
�״�·������ɽ������Ϊ������ɽ�Ž���̫���ĵط�����һ��·���Ա����ɽ���Ҳ���غ�ֱ�ӵִ�⸣���ڵ���Ļɽ��ԭ��û������·ʱ������ɽ��������һ�棬��������������߽�ȥ��
����ֱ����ĩ�и��ж�������˱�����������ɽ�µ������壬����ɽ�ű��˾������𣬵�Ȼ�����黭�硣����˵���������й��滭ʷ�ϣ����Ҳ�����λ�黭����������������ǹ㷺��ע��̽�֡��о��ͽ����
��������˵�����峯��������ֽ�����ɽ�������һֱ������������ע�����ҶԴ˵��˽����żȻ�����DZ����ʹ�����ݰ��ԲԵ�ʷ���������ȼ�λ֪���IJ������ר��ѧ�ߣ�������Һܼ�����˵������̫��֮��������ɽҰ���ĵ��̷dz����Ӧ�����Ʊ�����������ã������磬�������Ĺ����̫�����ϵ������������һ���������������˺�ѧ��Ľ�������ˣ���
���������Ҷ�����ɽ��ʼ���⡣һ����;��������ʱ���������³�������ɽ��´�����С·һֱ�ߵ�����ɽ�����꼻��֡�����ʱ��ͬ����˵���������Ĺ��������ɽ���
�����ҵ�ʱ��̧ͷ��������������ֻ���������ƽ�㣬��Ϊ�����ɣ����ʱ�dz��ģ�����������ɽΧ֮�£��ǹ�������ɫ�������ԲԴ���������ľ��
����������ط�����������㰵�����˵�ͷ����ϲ����һƬԭʼ��������
����Ȼ����ҹ����ʷʱ��������䣬�������������ǰ��ȥ����ɽѰ�ö�Ĺ�����֣�ʮ��������壬���ҿ��ý����ζ����һ�Σ����������ȥ�ˡ�
�������ڣ��ڶ��յ�ij����ĩ���Ҵ�绰Լ���ص�һλ��������ȥ����ɽ������λ�����������ң����������;�ʮ�����һλ����ר��ȥ����Ѱ�ù���Ĺ��
������������Լ�����������
�����Ⱦ������飬·��ԽϪ����ʱ����·���б����µ�ָʾ�ƣ����Ƚ�ȥ��һ��������������ɽ��ɽ�����ƽ���㣬��ֲ��ľ�����д�ׯ���ȵ�Ⱥɽ���࣬����һ��ɽ��ׯ���������״���ѱ���Ϊ��Ĺ�������¾���ɽ�ȶ��࣬��ɫ��ǽһֱ����ɽ�ţ�ǽ����һ���������ϼ��ţ���ǰ��һ�µ�ʯ��¥������¥��ʯ�ţ����������ӳ��һƬ����֮�С���20��2��
�������½�û���꣬���滹û�깤���Ϳ��ŵ�һλ���������˼��䣬��˵�������µģ��������µ���ʷ�ܹ��ϣ���һ��Ƭ���ر�������������
�����뿪�����¼���ǰ�У�ԽϪ�ѱ��滮�ͽ���Ϊ��ҵ��������ԭ�ȵ���Ȼ���䶼����Ǩ����Ұ�������·�������Ƭˮ�೧����ԽϪ�������ڣ�����Ҳ�±���һ���㽭��ҵ�����������������ʣ�������ʩ�Ŀ���Ѿ���á�
��������ζ�ţ�ԭ�Ⱦ��Խ���������̫��֮����Ҳ�����������ˣ�
�����������̫������һ·���������⣬�ұ�����Ұ�������ɽӰ����߱���������«���ݻƣ�������ͷ��б���յú�ˮ������
�����ڽ�������ɽ��ǰ���ȿ�������ʯ������ɽ�ڴ�Ƭ������ͱڡ��м����������ڻ���һƬ�IJ�ɽ��ʯ������ɽ�壬Ϊ����������ɽ�ŵIJ�ʯ崿�Ҳ�ɻ������أ���ԼҪ������Ƿ��ӡ�
������·�ں�ɽ�����ѡ��������ߣ�ɽҰ��Ȼ�ķ�ζ�������������������ڴ�ͣ�������ﴣ��һ���й�꼻��ֵĴ����ƣ�һ����·������ɽ��С��ׯ���������������죬��˳ɽ�ƹ��˸��䣬꼻��־������������������ײ���ɽ���¡�����ǰ�ż��������ڴ�����ľ�˽��µķ��ӣ�ԭ�����羫�µ�С�֣����ºܿ�ͽ�����Ϊ��ɽ¶ˮ�Ĵ����ˡ�
������꼻���ԭ·���أ���·�����ȵ���ǰ��·����ԭʼ������·��ǰ������¹��꣬·�氼��ƽ�����dz���ѹ�ݵ�ӡ�ۣ��е�����ﻹ�л�ˮ����Ҷ�ѹ��ˮɼ��·���߶϶����������г�ɢ��״�Ķ��Σ��ڶ���������������ɫ�ģ�����ʮ����������
����;��ѯ�����ˣ��������Ĺ���������𣿴��ǡ����������ʲô�ط������˾�����������һָ���������档
�����������ɽ��ܿ���������ɽ�ʡ��硱���Σ��������г������ֵĴ�̫ʦ��һ�㣬�ڶ�������ķ��ִ�������һ��С������ɽ����������м��ǹ�����ƽ����ɽ�µأ������˱���ɣ�����ԡ��������顡������վ
����Ϧ���е�����ɽ���㻹�ܰ�����ã���2��
���������߽�ȥ��Щ�أ���
�������Ӷ���·�ڽ�ȥ����ũ��ңָɽ��Ķ��ࡣ
�������ǻص����ߴ�·���Ĵ������嶫ɽ�Ž�ȥ����ͬ����һ��ԭʼ���С·�����ߣ��ƹ�һ�ù����µij����������м��Ƭɣ���ѰѰ���٣�����ʲô�أ�
����ͻȻ����������һ�߽�������������������
����æתͷȥ����������ָ�Ÿ���ɣ��һ��������������
������ǰһ������Ȼ��һ�����أ��ӷ�ǰʯ���ɼ�Ϊ����������������һ��ʯ��������ǰ����һ��ʯ����Ҳ˵����Ϊ��Ĺ������Ϊ�����ı���λ��
�������ڵͰ���ɣ�����У���Ϊһ��¡��Ļ�����ѣ���ª�������������ţ�����Ƕ������Ĺ��������
����һ��һ��ߵ����������������Ҷ�ӣ������ŷر߹������վ�ţ���ɫ֦���ϲ������ҵĺ�ɫ���١�
��������������տ���ɣ����վ��һ�ᡣ��ǰ�������Ĵ�������˵����ص�ѡ��һ���ˮ���ѵ�λ�á�Ȼ��ָ����ҿ����˷�λ����Χ��ɽ�������ģ������̫������������������������п���ǰ���գ����������࣬���Һ����������ɵ��㸡�ּ�������ɫ��ɽӰ����ʼ�һ�㡣
�������ǰ�ɽ�������DZʼ�ɽ����ˮ���ѣ���˵������������ֻ�����������ıʼ�ɽ��һ�ڹ⸣��һ������ɽ���
��������ɽ�������̫��������δ�����߹�·ʱ���Ӹ�����Ĺɽ��ȥٲȻƯ�����У����з��������������������ʱ���Դר����Ѱ��Ĺ��ֻ�ܷ�ɽԽ�룬������������������°�����꣬�����������߷��н��IJ����С����Դ��һ��ǰ�����ɵ�ξɽ��´����������о�ɣ�����ֿڡ������֡����ա���������´��Լ����u�����룬����ɽ������������ʱ�ɶ������������Ĺǰ��Ĺʯ�̡�����������Ĺ�������ĩ���б�Ĺ�Ὠ���������顱�����Ĺʯ�������ڣ������ҽ��쿴������顣����ʱ���Դ�����Ķ�Ĺ�����ҷ���һ���ѣ�������������һ���ѣ����ҷ�����Ϊɣ��
������ʱ�����Դ�ղ�����Ȼ�����҉V֮��Ϊ��⸸��֮�V�����ڴ�����ѯ���ʵף��ֱ�Ѱȫɽδ���ټ������������ڶ���ɣ�ߵ�һ�������������Ϊɽ����֮��ʯ���ְ�ģ��������ν�����������һ���ﲻФ������ɽ������ij�����������������P��������ij���Զ������ɽ֮�⡣���Դ��������δ��֮ʱ���߷����ԣ�������������ߣ���Ű��ݡ�
�����ϸ����͵����飬����ʮ���ȥ�ˣ����������Ȼ�����в��������ʣ�Ҳ�����Դ����һģһ����
�������Դ�����뿪��Ĺ����ȥ������֣��ɼ�Ϊ��꼻��֣������յǷ�����������ɽ��ʤ����ɳ��Ҷɽ�������У��羰���ѡ���ʱ���Ϸ���𣬺�����ӿ�����ɣ�ӭ�����˶�������ʱ��̾���������۳���ǹ��������⸣��ɽ���Դ�Ϊ��ʤ��ʯ�ڴ�֮������ѷ��Զ�ӣ���
������ϧ��δ������һ���dz��������۳���ǹ�����̫����ӿ����������������ɽ´������̫�����Dz���Ϧ���������İ����̡�
��������ҹ�������DZ��������ɽ�ǡ���ʮ�ֵ���Ȥ��ζ����¼ȫ�����£�
��������ɽ������ͤ����ȡ��Ϊ����Ҳ��ɽ��̫��������ԪĹɽ������Ĺɽ����Ԫ����֮���������ڼ����£��ɸ���ʰ���谮ɽ֮�����������ɡ�ȡ����ɽǮ�ҿ������壬һ·��÷���У������Ӱ��������ӣ�����������䣬�����������غ����У��廷���ۣ�ʼ��������ö���Զ����ʮ�����������壬����������ڴˡ�������¹��״���������������˲�������������������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