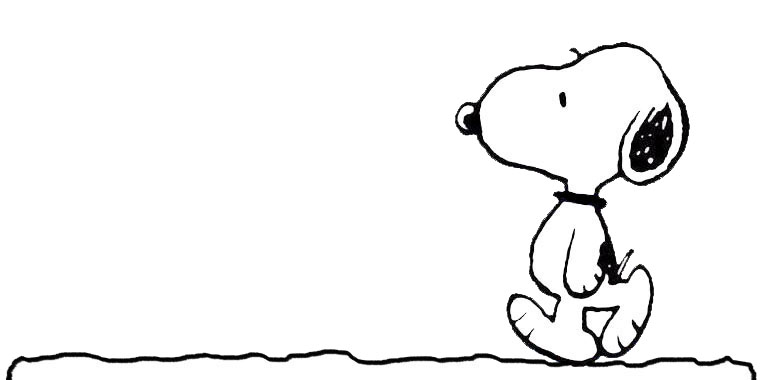胡也频作品集-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校中,每次写信给双亲的时候,我曾想——其实是因想到她,才想起给家里写信,但结果都被胆怯所制,不敢探问到她,即有时已写就了几句,也终于涂抹了,或者又连信扯碎。
第二年的夏天,我毕业了,本想借这机会回家去,好生的看望她,向她说出我许久想念她的心事;但当时却突然由校长的命令(为的我是高才生),不容人拒绝和婉却的,把我送到战舰上去实事练习了。于是,另一种新的生活,我就开始了,并且脚踪更无定,差不多整年的浮在海面,飘泊去,又飘泊来,离家也就更远了。因此,我也就更深的想念着她。
时光——这东西像无稽的梦幻,模糊的,在人的不知觉间,消去了,我就这样忽忽的,并且没有间断地在狂涛怒浪之中,足足的度过六年,我以为也像是一个星期似的。
其实,这六年,想起来是何等可怕的长久呵。在其间,尤其是在最后的那两年,因了我年纪的增长,我已明瞭所谓男女之间的关系了,但因这,对于我从幼小时所深印的她的影子,也随着更活泼,更鲜明,并且更觉得美丽和可爱了,我一想到她应该有所谓及笄年纪的时候,我的心就越跳跃,我愿向她这样说:我是死了,我的心烂了,我的一切都完了,我没有梦的背景和生活的希望了,倘若我不能得到你的爱!——并且我还要继续说——倘若你爱我,我的心将充满欢乐,我不死了,我富有一切,我有了美丽的梦和生活的意义,我将成为宇宙的幸福王子。……想着时,我便重新展览了用全力去珍重保存的那些纸折的物件,我简直要发狂了,我毫无顾忌地吻她的那个纸塔——我的心就重新挟击着两件东西:幸福和苦恼。
我应该补说一句:在这六年中,我的家境全变了,父亲死去,惟一的弟弟也病成瘫子,母亲因此哭瞎了眼睛,……那末,关于我所想念的她,我能用什么方法去知道呢?能在我瞎子的母亲面前,不说家境所遭遇的不幸,而恳恳的只关心于我所爱恋的她么?我只能常常向无涯的天海,默祷神护祐,愿她平安,快乐和美丽……!
倘若我无因的想起她也许嫁人,在这时,我应该怎样说?我的神!我是一个壮者,我不畏狂涛,不畏飓风,然而我哭了,我仿佛就觉得死是美丽,惟有死才是我最适合的归宿,我是失去我的生活的一切能力了。
不过,想到她还是待人的处女的时候,我又恢复了所有生活的兴趣,我有驱逐一切魔幻的勇气,我是全然醒觉了,存在了。
总而言之,假使生命须一个主宰,那末她就是主宰我生命的神!
我的生活是建设在她上面。
然而,除了她的眼光和微笑,我能够多得一些什么?
这一直到六年之最末的那天,我离开那只战舰,回到家里的时候……
能够用什么话去形容我的心情?
我看见到她(这是在表姨妈家里),她是已出嫁两年了,拖着毛毵毵黄头发不满周岁的婴儿,还像当年模样,我惊诧了,我欲狂奔去,但是我突然被了一种感觉,我又安静着;呵,只有神知道,我的心是如何的受着无形的利刃的宰割!
为了不可攻的人类的虚伪,我忘却了自己,好像的忘却了一般,我安静而且有礼的问她好,抚摩她的小孩,她也殷勤地关心我海上的生活情况并且叹息我家境的变迁,彼此都坦然的,孜孜地说着许许多多零碎的话,差不多所想到的事件都说出了。
真的,我们的话语是像江水一般不绝地流去,但是我始终没有向她说:
“表妹,你还记得么,七年前你折叠的那个纸塔,还在我箱子里呢!”
北京沙滩
北风里
纸窗上沙沙沙沙的响,照经验,这是又刮风了。
这风是从昨天夜里刮起的,我仿佛知道。刮起风来,天气又变了。我刚刚露出头去,就觉得有一种冰凉的东西,湿湿的贴到脸上来;棉被里面是暖和得多了。
“这样的天气,怕要冻死人呢!”我想,便缩下头去。
在平日,我有一种习惯,是醒来就穿衣,就下床,然后看报的。这时却异样了,拢紧一下周身的棉被,让整个身体在小小区域的温暖中,多挨一会儿;而这挨,在这样天气奇冷的北风哮叫时候,可算是一种幸福罢。
因为挂念着自己的文章被登载了没有,想看一看《太阳报》的副刊,便又露出头来,喊伙计……可是赶紧的就把这声音拉住了,这是忽然想到,欠了送报的两个月报费,前天的报就给停送了。
没有报看,眼睛便往别处去溜,却发现那墙上的一个小窟窿,圆圆的,忽露出一个尖形的小小的嘴,那嘴上,又闪出两小点黑色的光。
“哈哈,这原来就是它们的案!”我想到无论在白天或灯光底下,无意中常常见到的那些黑毛柔软的小动物,胆怯地四顾,悄悄地走,张着弱小却伶俐的眼,游行在我的书架和桌上,就是躲藏在这个小窟窿里的。
于是又照样,一个两个,连续地出来了,最后的那个是更小而更机灵的;它们是彼此观顾,把翘起的长须去表示本能的作用,大家贼似的,慢慢地走,成为一个极安静的又滑稽又可怜爱的小小的行列。
发现着这些耗子,这独寝的客舍,便显得更寂寞。
“该剩一个馒头来……”我想,然而因怕冷,我的头又缩到被里去了。
那一小群的耗子也许还在觅食而游行,而终于感到失望吧,但我不去想这事了。我这时填满在心头的,依旧又是那天气的冷。
天气冷,冷极了,可以生起大的火炉来,凭那火,熊熊的,把房子里面变成了春末天气,人只要穿夹衣,——这样的过着冬,冬天似乎也并不可怕了。我想。
然而我忽然觉得,从上海晨曦书店寄来的稿费,用到昨天,所剩在衣袋里的只是两张(或三张)二十枚的铜子票,和几个铜子了,火炉虽然可由公寓里按月租价一元的代安下来,但是煤,这煤的来处却难了。煤,至少要买二十五斤吧,倘若一百斤是九毛,也得两毛又十枚,而这数目我就无法凑足了,而且——生火还得要劈柴呢。
常常被两三毛钱所困住,这真可恼。但这穷,虽说可恼,却因为是常事,随着也就爽然了。且觉得在这个时代里,炮火是人心追逐或欣慕的宝贝,一个著作者被人漠视,正是应该的。其实,即有了那么太平的时候,在一切都比别个民族沉寂和冷淡的国度里,著作者能得到什么人都应得的两种生活的享受,也不见得。
“那末,你改造好了!”我又向自己嘲笑。
改途,这或者能攫得较好的生活,并且要远离艰苦,似乎也只有这改途的一端了。但是我,虽说曾常常对于著作者生涯的惨淡而生过强烈的反抗,而转到悲观去,却究竟是生平的嗜好,无法革掉了。由是,那所遭遇的穷况,不正是分所应得的么?
然而事实到底是事实,每因穷,把一切的愤怒都归到稿纸上去,而且扯碎了,团掉,丢到烂纸篓里,是常事。
可是,要生活,终须靠住那稿纸填上蓝色或黑色的字去换钱的;因而在许多时候,稿纸变成生命似的顶可爱的东西,而且对于那些扯碎的又生起很歉疚的惭愧了。
“如果命运有分做幸与不幸,那末,象这样生活的著作者,便是属于那不幸的!”我常常想。
今天因为没有钱买煤,我所想的又是这些事。
开头想这些事的时候,是苦恼,而且带点愤愤的,到最后,这恶劣的情绪却安静了,于是我又平心的向事实去着想:
躺在被窝里,温暖固然是温暖了,而想就这样的尽挨下去,不吃饭,不看书,也不写文章,这究竟是不很妥当的事,因为天气既然骤冷起来,说不定是延长的更冷下去了。那末,火是必须生,煤也就应当买,是无疑的。
“那只有这办法!……”我想,决定了,便露出头来,并且把整个的身体离开那小小的温暖的世界,下床去了。
风还在窗外乱叫,可怜爱的小动物的行列却不见了,但在房子里,是依样充满着冷气和寂寞。
我从床下拖出一只旧的黑色的木箱来,轻飘飘的,而这感触,猛然就使我惘然了。我知道,在这箱里面,所余剩的,只是一件烂了袖口和脱了钮子的竹布长衫,和两三条旧的或破裆的短褂裤,以及几双通底的麻纱袜子,还有的,那就是空气了。
我无力的把箱盖盖下来,眼光从这满了灰尘的木箱上面迟缓地望到墙上去:那里是一张放大的雪莱的像,在下面,偏左些便是那个颇深的圆圆的鼠穴。
“这洞,这样圆,和洋钱差不多……”
眼光从这窟窿上转移到别处去,全是黯淡的纸糊的壁。
我踌躇了。对于这唯一的计划的失败,是出乎意外的;但这时,既下了床,又不愿再滚进被窝去。那自然要想出一个法子。
在这种的情形底下,最方便的,自然是抽出屉子来,或伸手到衣袋里,忽然发现到在什么时候忘却的一张钞票或一块洋钱,——然而这无望。其次呢,就是向附近的朋友处去拿,而这,又艰难,因为较阔的象官僚气派的朋友是从来没有,就少爷模样的朋友也难得,而光棍的朋友其情形当不会两样,或许是更窘了。又其次,是想来一个恩人似的不速之客,这却是,类乎很滑稽的可笑的梦了,更难实现的。
各种从模糊思想中出来的希望全无用,这使我更费踌躇了。
眼睛又不自主的向四处去溜,慢慢地就光顾到单薄的那两条棉被和一只丁玲君送给我的鸭绒枕头。
“那只有这办法……”我又想。
这枕头买来是花八元钱,要是当,两元至少一元总可以吧,可是当铺的先生们不要这东西;棉被在冬天里放到当铺的柜台上,这差不多是奇货,是很可以抬价的,但一想,这样的冷天,到深夜时,一个不是粗壮的身体只盖着一床棉被,而且是又旧又反又单薄的,倘因此受了凉,病了,不是更坏的事吗?
在眼睛里是绝望的光,却转动了,于是又看见那清秀的诗人雪莱的像,以及那个象洋钱形状的鼠穴。
这时有一种希罕的感觉通过我的脑,我心想,却笑起来,但接着就黯然了,——是想把这诗人的遗象去解决我的难题!
诗人的象在放大时是花了四元,镶在一个价值二元的一只木框上,从数目算来,共是六元钱,那末,变卖了,至少总可以得一半的价,是三元。我想。
然而我的心,立刻就浮上罪恶似的,非常的惭愧了。但在我的眼睛里,年轻的诗人,依样是英俊的,且带着女性的美,静默着。
一阵更大的风把纸窗打得急促的响,我便抖了一下。
“真无法……”
于是我跳上桌子,从墙上,拔出一寸多长的铁钉,连着很长的白色棉纱绳,把雪莱的像拿下来了;在手上,木框是冰块一般的冷。
抹去了玻璃上的灰尘,很歉疚的挟着诗人的像,出去了。
北河沿的浅水已冻成坚实的冰。柳树脱去了余留的残叶,剩着赤裸的灰色的枝,象无数鞭条,受风的指挥向空中乱打。很远处都不见一只鸟儿。浑浊的土灰从地上结群的飞起,杂着许多烂纸碎片,在人家的门前和屋上盘旋。行人都低着头,翘着屁股,弯着腰,掩着脸,在挣扎模样的困难的迈步。洋车夫抖抖地扶着车把,现出忧郁和仿惶的神色。发威一般,响在四周的,是北风的哮叫,却反把这平常颇热闹的街道,显得更萧条冷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