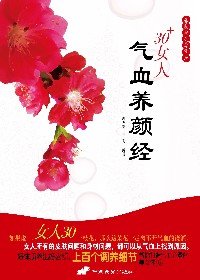洛杉矶的女人们-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然后你把记录打出来,他们的问题,你的回答——不要走样——一字不漏。我们要见一次面。明天,我把阿尔玛带到棕榈泉,预计安排一周,我是说她能呆一周。因为太重要,我本人要提前赶回。星期五,我们就在这里见面——工作时可以共同晚餐。这些安排适不适合未来的编辑?”
“我想这是个绝妙的主意。”
“我回来后,星期五,我会打给你电话……我想那是阿尔玛到门前了。”他一跳站起身。“把一切都记下来,记转—三部分。”
“我忘不了,福斯特先生。”
只有在后来,当厄苏拉来到布里阿斯要向她的街道转弯时她这才记起来,她说好要和哈罗德见面的。她原答应要见他——她抬起手臂,眯起眼看了一下手表——过去10分钟了。
她答应和他一起看看他的新办公室,帮他装饰和配备一下。
呐,她可以打电话解释一下,说她脱不开身。后来,她突然记起来,他目前不再需要那间办公室了。他们要向东搬。她可以帮助他,甚至为他雇个装饰师。这样做自然表示出她一直在想着他,难道不是吗?
※※※
萨拉·戈德史密斯仰躺着,闭着眼睛,手臂举在前额上。
她的呼吸仍是短促的吁吁声,她的心脏呼呼地跳动,从宽大臀部到双脚的里面,已经耗尽和疲竭。她感到身边的床动了一下,接着她感到弗雷德的多毛的大腿触到了她的大腿,并用大腿戏要着蹭磨她的。他的脚趾触到她的脚趾,并弯起来抓挠她。她眼睛仍然闭着,想到刚刚度过的时光,想到他们之间不停顿的经久不衰的奇迹,不禁微笑起来。
“我爱你。”她悄声说。
“你是我的。”他说。
“全属于你。”
她懒洋洋地睁开眼,意识到的是海蓝色的大花板,然后向前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她的胸部宽大的白色隆起,然后是薄薄的白色棉布床单,它遮蔽着那乏力的一丝不挂的身体的剩余部分。对着的墙壁上,梳妆台上面斜挂着的镜子反映出樱桃木踏脚板,再看不见别的。她在枕头上转了一下头,让她眼睛对着她的心上人尽情地欣赏了一番。
他同样仰躺着,双臂放在枕头上。她又一次地对他的躯体的力量感到喜悦。那是一种原发的力量。他那缠结的黑头发、低眉毛、糙鼻子、突出的下巴、有力的溜肩、粗脖子、宽厚的胸堂,一派永葆活力的有前途的形象。第一次见到他时,她记得,他那副穴居人的外貌,虽令人感到兴趣,但也使她失望。
尽管她听说他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她还是想象不出,这样一副尊容怎么能够容纳下灵感和高智能。后来,他那柔软悦耳的话音、他头脑深邃的入木三分的理解力、那不可思议的广博的能够包容莎士比亚和坦尼斯、威廉斯的学识,是那样的与他外貌不配称,把她完全折服了。
稍稍在他身边过去一点的沙发椅子上,她看见了衡量她的愿望和情欲的标志。她的衣服被匆忙地、毫不顾及地扔在一堆——她的上衣、她的裙子、她的乳罩、她的尼龙内裤——只有那件皮茄克,她首先脱下来的东西,尚被仔细地搭在椅子的靠背上。她从皮茄克的口袋里可以看得见,突出在外的一张明信片和几个信封。她记起来:在她急急忙忙出来到停车场时,她被邮递员叫住了一下。进入小客车之后,她曾瞥了一下这些邮件,有一张神秘的邮卡——5月28,星期二,9点至10点15分——后来,因为她晚到了半小时,一时的匆忙,竟把它忘了。现在,她也搞不清,究竟是什么让她把这张明信片带到弗雷德的住所来。什么也不是,她想。她不过一时忘却罢了。
她见他轻微地一动。“你在想什么?”他问。
她看着他。“我多么爱你可。我不知道没有你我怎么活。”
她思考了一下。“当然,我没有你活不下去。我没有一个细胞、一次喘气是活着的,直到我遇到你。”
他点点头。“当爱情说话时,那是所有神圣的声音,使上天也会在和谐之中打瞌睡。”
“那指什么?”她问。
“姻缘天定。”他高兴地说。
“我有时想已经过了一百万年了。你知道多久了吗,弗雷德?”
“一百万年。”
“不,3个月零两天。”
他转身侧肩躺着,这样他的前胸碰着她的胳膊,而他的头就放在她的肩上。他的手找到她的脖子和她肩上的弯曲部位。
他缓缓地,温柔地抚摸着她。
她合上眼睛,任凭自己去享受这种甜蜜的感觉,不过,她只让身体享受罢了。她的思想早已向国旅行过去——旅行回1个月、2个月、3个月零两天以前。
事情的起始是与《她屈尊以求》一出戏的业余演出有关,是由布里阿斯妇女联合会为了慈善事业发起和演出的。格利斯·沃特顿的记录上,有萨拉15年前曾在大学的演出中露过面的话,于是便求她候选出演。萨拉直截了当地谢绝了。后来,厄苏拉·帕尔默,因她答应过帮办一夜演出的宣传,便劝说萨拉。后来她便同意陪同厄苏拉,因为那天让孩子闹得很不愉快,也因为她感到有些腻烦。不过,在候选前夕,她又一次地改变了主意。萨姆实在忍受不了她的越来越厉害的焦躁不安的情绪,与她在整个吃晚饭时间里不住地吵嘴辩论——他认为那是一种娱乐,可以成为一种乐趣,每周离开家到外面呆几个晚上会有好处的。但她就是顶着不去。吃过饭后,当她清理餐桌,看见萨姆将他那大块头的身躯安放在电视机前时,她这才知道,她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令人麻木单调的生活了。她即刻打电话给厄苏拉,一小时后,她便来到寒冷的妇女联合会的礼堂,加入到其他二十几位有演出经验的妇女和几位丈夫及未婚夫的行列中。
她现在回想起,他们都聚集在前面的一二排等着他的到来。格雷斯·沃特顿的丈夫认识一位电影制片商,这位制片商认识一位著名的导演,介与影视界中间,此人就是弗雷德·塔帕尔。这次既然是很有分量的义演,他同意执导。他出现了,顺着中间通道大步走过来,军用胶布雨衣像斗篷似地搭在肩上,对格雷斯和其他聚集在那里的人作了自我介绍。他为来晚了和不加考虑地就接受了这份差使感到歉意。情况并非这样——他即刻进行解释——他不是在影视圈里,电影已不再存在,人们对它不再感兴趣或者去看它,电视才是流行的腐败东西。他手头有很多电视脚本,不过他不想成为由麦片或牙膏主宰的任意电视的辅导员——不过,吸引他同意执导该剧的原因,是因为他这块正统舞台的创造力,他喜欢奥利弗·戈德史密斯,他想这可能很有娱乐性。
萨拉想,他并不漂亮,有些骄傲,尽管他的讲话异常安详和动人。在舞台上,他每次召唤八位候选人,他们坐在折叠椅子上,战战兢兢地读着,而他却在台上来回踱着步子。萨拉是随着第二批登上舞台的,后悔离开她那家庭的墓穴并背离了她原说不来的话。轮到她时,她读的是卡斯坦斯·内维尔的一段,内维尔是托尼·鲁坡金的表妹,是哈斯丁的爱人。在她开始读时,弗雷德·塔帕尔没有看她一眼,一直在来回踱着步子。突然,他停住了,直盯盯地看着她,厉声说:“我听不见你。”她咽了口唾沫,读大声一些——而他则继续盯着她看。不出5分钟,她读完了她的角色。这便是事情的开始。
弗雷德·塔帕尔决定,每周排练几次,共排练六周。开始在礼堂里排练,不过很快便搬到弗雷德住处的大起居室里,这地方距贝佛利山的威尔瑟大街南只有两道街面。在这样一次排练之后,弗雷德邀请萨拉第一天晚间单独去一下,进行某种私下强化辅导。他的态度是那样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用过火热的眼睛盯着她看),于是她答应出常她把孩子安排上了床,让萨姆舒适地留在电视机前,9点钟到达了弗雷斯的住所。他手里拿着剧本,在门口迎接她,那种友好态度她从未见他有过。当他建议喝杯酒时,她即刻接受了。晚饭后她很少喝酒,不过她有点紧张和害怕,觉察到她是在某处未探明的地区的边缘。一杯变成两杯、四杯、六杯,排练的事老早就放弃了,而她现在就坐在他身旁,她已不感到害怕了。
一切都是朦朦胧胧的,这是几周来——不,几月来,多年来第一次毫不拘束的欢娱。他对她诉说他的人生,诉说那个他已分离的女人,那个可怕的不想与他离婚的生物。而她也对他诉说起萨姆,过去虚度的年华和孤独感。后来,他握住了她的手,这以后她再也记不起是她吻了他,还是他吻了她。只记得他们搂抱在一起好长时间。只记得他们走进卧室时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他为她脱衣服时,她晕乎乎地站在床边。这以后,他一直吻她直到她想尖叫出声。他将她安放在床上,她直挺挺地躺在那儿,紧紧地闭上眼睛,这样她就不可能看见,用闭而不见的办法就可避免成为犯罪的主动者并且不会感到害羞。她感觉到他就在她身边,抚摸她,最后她用手抓住他。这举动使她自己都感到吃惊。她想快干,干那种可怕的事情。那事干了,不可挽回地干了,当他把自己的身体与她的交织在一起时,她曾希望那事就像她与萨姆总是那么快速一样尽快地干完,这样,就不再有她的一部分了,而她也不再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不正当的事情的一部分了。她等着那事快被干完,等待着,等待着。后来突然之间,不由自主地她成了这事的一部分,她竟用从来没有干过的那样动作起来,有一种她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感觉,并且希望它永远来到,永远别结束。
早上,在她的厨房里,她回避去看萨姆和孩子们在用餐的桌子。她感到悔恨和有些宿醉,在她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兴奋和有活力。她打算退出排练,从自己那里藏掉那羞耻的一幕,不停地让自己确认,这是一个因酒兴发作引起的偶发事件。可是,当夜幕垂临时,她知道她又不想从这个剧中撤出来。她开始计数到下次排练还需等多少小时,仍在朦朦胧胧地意识到那座曾住过的,并与那个外人同共分享过的陌生的房子。
三个夜晚之后,她与那组人一起,在弗雷德的住所参加了另一次排练。她有时纳闷,她竟能排演得那样地正常,弗雷德的举止竟像他平常的那样自然,她机械地说着台词,心下猜想他在想什么。到了11点,排练中止了。当她去取她的上衣时,他礼貌地问她能否晚走停留10钟,再排一次第一场的一段话,这段话他还不放心。她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话,留在后边。这一次,他们没有喝酒,几乎连话也没有说。这一次,不再是什么酒后失态了。第二天早上两点钟,她驱车回家时,她感到像一个嗜酒狂那样没有责任,无忧无虑。
排练结束了,剧继续演下去。台词忘记了,道具也被乱堆一气。尽管如此,最后的帷幕还是降下来了。掌声雷动,义演成功。再也不可能有夜聚了,或者极少有了。那桩事变成了在上午举行的仪式,一周四或五个上午。她的贪得无厌使自己吃惊、震动并感到快活。这个偶尔开始的事情变成了一种必需的习惯,成为每个生活的一天和将要生活的一天的绝对含义,其结果是可以想见的——因为它是不现实,毫无目的,甚至是危险的。可是,尽管如此,萨拉硬是不让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