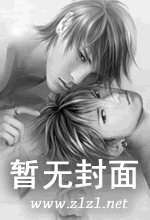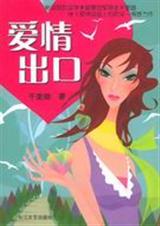出口成章-第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骆驼祥子》因为是长篇,又比《上任》与《月牙儿》,无论在思想上与描写上,都更明确细致了些。可是,我到底还是不敢高呼革命,去碰一碰检查老爷们的虎威。我只在全部故事的末尾说出:“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祥子,不知陪着人家送了多少回殡;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埋起他自己来,埋起这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这几句在节录本中,随着被删去的一大段删去。)我管他叫“个人主义的末路鬼”,其实正是责备我自己不敢明言他为什么不造反。在“祥子”刚发表后,就有工人质问我:“祥子若是那样的死去,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无言对答。
以上,是我乘印行这本选集的机会,作个简单的自我检讨。人是很难完全看清楚自己的,我说得对与不对,还成问题。不过,我的确知道,假若没有人民革命的胜利,没有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明确的指示,这篇序便无从产生,因为我根本就不会懂什么叫自我检讨,与检讨什么。我希望,以后我还不偷懒,还继续学习创作,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那么去创作。
载一九五○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
人、物、语言
在文学修养中,语言学习是很重要的。没有运用语言的本事,即无从表达思想、感情;即使敷衍成篇,也不会有多少说服力。
语言的学习是从事写作的基本功夫。
学习语言须连人带话一齐来、连东西带话一齐来。这怎么讲呢?这是说,孤立地去记下来一些名词与话语,语言便是死的,没有多大的用处。鹦鹉学舌就是那样,只会死记,不会灵活运用。孤立地记住些什么“这不结啦”、“说干脆的”、“包了圆儿”……并不就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北京人来。
我们记住语言,还须注意它的思想感情,注意说话人的性格、阶级、文化程度,和说话时的神情与音调等等。这就是说,必须注意一个人为什么说那句话,和他怎么说那句话的。通过一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生活与性格来。这就叫连人带话一齐来。这样,我们在写作时,才会由人物的生活与性格出发,什么人说什么话,张三与李四的话是不大一样的。即使他俩说同一事件,用同样的字句,也各有各的说法。
语言是与人物的生活、性格等等分不开的。光记住一些话,而不注意说话的人,便摸不到根儿。我们必须摸到那个根儿——为什么这个人说这样的话,那个人说那样的话,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必须随时留心,仔细观察,并加以揣摩。先由话知人,而后才能用话表现人,使语言性格化。
不仅对人物如此,就是对不会说话的草木泉石等等,我们也要抓住它们的特点特质,精辟地描写出来。它们不会说话,我们用自己的语言替它们说话。杜甫写过这么一句:“塞水不成河”。这确是塞外的水,不是江南的水。塞外荒沙野水,往往流不成河。这是经过诗人仔细观察,提出特点,成为诗句的。
塞水没有自己的语言。“塞水不成河”这几个字是诗人自己的语言。这几个字都很普通。不过,经过诗人这么一运用,便成为一景,非常鲜明。可见只要仔细观察,抓到不说话的东西的特点特质,就可以替它们说话。没有见过塞水的,写不出这句诗来。我们对一草一木,一泉一石,都须下功夫观察。找到了它们的特点特质,我们就可以用普通的话写出诗来。光记住一些“柳暗花明”、“桃红柳绿”等泛泛的话,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泛泛的词藻总是人云亦云,见不出创造本领来。用我们自己的话道出东西的特质,便出语惊人,富有诗意。这就是连东西带话一齐来的意思。
杜甫还有这么一句:“月是故乡明”。这并不是月的特质。月不会特意照顾诗人的故乡,分外明亮一些。这是诗人见景生情,因怀念故乡,而把这个特点加给了月亮。我们并不因此而反对这句诗。不,我们反倒觉得它颇有些感染力。这是另一种连人带话一齐来。“塞水不成河”是客观的观察,“月是故乡明”是主观的情感。诗人不直接说出思乡之苦,而说故乡的月色更明,更亲切,更可爱。我们若不去揣摩诗人的感情,而专看字面儿,这句诗便有些不通了。
是的,我们学习语言,不要忘了观察人,观察事物。有时候,见景生情,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情加到东西上去。我们了解了人,才能了解他的话,从而学会以性格化的话去表现人。我们了解了事物,找出特点与本质,便可以一针见血地状物绘景,生动精到。人与话,物与话,须一齐学习,一齐创造。
语言、人物、戏剧
——与青年剧作者的一次谈话
要我来谈谈创作经验,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几句关于戏剧语言的话吧。创作经验,还是留给曹禺同志来谈。
写剧本,语言是一个要紧的部分。首先,语言性格化,很难掌握。我写的很快,但事先想得很多、很久。人物什么模样,说话的语气,以及他的思想、感情、环境,我都想得差不多了才动笔,写起来也就快了。剧中人的对话应该是人物自己应该说的语言,这就是性格化。对一个快人快语的人,要知道他是怎样快法,这就要考虑到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剧情等几个方面,然后再写对话。在特定时间、地点、情节下,人物说话快,思想也快,这是甲的性格。假如只是口齿快,而思想并不快,就不是甲,而是乙,另一个人了。有些人是快人而不快语,有些人是快语而不是快人,这要区别开。《水浒》中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人物,都是农民革命英雄,性格有相近之处,却又各不相同,这在他们的说话中也可区别开。写现代戏,读读《水浒》,对我们有好处。尤其是写内部矛盾的戏,人物不能太坏,不能写成敌人。那么,语言性格化就要在相差不多而确有差度上注意了。这很不容易,必须事先把人物都先想好,以便甲说甲的话,乙说乙的话。
脾气古怪,好说怪话的人物,个性容易突出。这种人物作为次要角色,在一个戏里有一个两个,会使戏显得生动。不过,古怪人物是比较容易写的。要写出正常人物的思想、感情等等是不容易的;但作者的注意力却是应该放在这里。
写人物要有“留有余地”,不要一下笔就全倾倒出来。要使人物有发展。我们的建设发展得极快,人人应有发展,否则跟不上去。这点是我写戏的一个大毛病。我总把力气都放在第一幕,痛快淋漓,而后难为继。因此,第一幕戏很好,值五毛钱,后面几幕就一钱不值了。这有时候也证明我的人物确是从各方面都想好了的,故能一下笔就有声有色。可是,后面却声嘶力竭了。曹禺同志的戏却是一幕比一幕精彩,好戏在后面,最后一幕是高峰,这才是引人入胜的好戏。
再谈谈语言的地方化。先让我引《红楼梦》第三十九回刘姥姥进大观园和贾母的一段对话:贾母通:“老亲家,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刘姥姥忙起身答道:“我今年七十五了。”
贾母向众人道:“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朗!比我大好几岁呢!我要到这个年纪,还不知怎么动不得呢!”
刘姥姥笑道:“我们生来是受苦的人,老太太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要也这么着,那些庄家活也没人做了。”
贾母道:“眼睛牙齿还好?”
刘姥姥道:“还都好,就是今年左边的槽牙活动了。”贾母道:“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我都记不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人笑话,我都不会。不过嚼的动的吃两口,睡一觉,闷了时,和这些孙子孙女儿玩笑会子就完了。”
刘姥姥笑道:“这正是老太太的福了。我们想这么着不能。”贾母道:“什么福?不过是老废物罢咧!”说的大家都笑了。贾母又笑道:“我才听见凤哥儿说,你带了好些瓜菜来,我叫他快收拾去了。我正想个地里现结的瓜儿菜儿吃,外头买的不像你们地里的好吃。”
刘姥姥笑道:“这是野意儿,不过吃个新鲜;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
这里是两个老太太的对话。以语言的地方性而言,二人说的都是道地北京话。她们的话没有雕琢,没有棱角,但在表面平易之中,却语语针锋相对,两人的思想、性格、阶级都鲜明地表现出来了。贾母的话是假谦虚,倚老卖老;刘姥姥的话则是表面奉承,内藏讽刺。“依我们倒想鱼肉吃,只是吃不起”,这句话是多么厉害!作者没有把贾母和刘姥姥的话写得一雅一俗,说的是同样的语言,却表现了尖锐的阶级对立。这是高度的语言技巧。所谓语言的地方性,我以为就是对语言熟悉,要熟悉地方上的一切事物,熟悉各阶层人物的语言,才能得心应手,用语精当。同时,也只有熟悉人物性格,才能通过对话准确地表现不同身份、地位的人物性格特征。
戏剧语言还要富于哲理。含有哲理的语言,往往是作者的思想通过人物的口说出来的。当然,不能每句话都如此。但在一幕戏中有那么三五句,这幕戏就会有些光彩。若不然,人物尽说一些平平常常的话,听众便昏昏欲睡。就是儿童剧也需要这种语言。当然写出一两句至理名言,不是轻而易举的。离开人物、情节,孤立地说出来,不行。我们对人物要想得多想得深,要从人物、情节出发去想。离开人物与情节,虽有好话而搁不到戏里来。这种闪烁着真理光芒的语言,并非只是文化水平高的人才能说的。一般人都能说。读读《水浒》、《红楼梦》,很有好处。特别是《水浒》,许多人物是没有文化的,但说出的一些语言却富有哲理。这种语言一定是作者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的。一句话想了又想,改了又改,使其鲜明,既富有哲理,又表现性格,人物也就站起来了。一个平常的人说了一句看来是平常的话,而道出了一个真理,这个人物便会给观众留下个难忘的印象。
以上说的语言性格化、地方性、哲理性,三者是统一的,都是为了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
平易近人的语言,往往是作家费了心血写出来的。如刚才谈的《红楼梦》中那段对话,自然平易,抹去棱角,表面没有剑拔弩张的斗争,只是写一个想吃鲜菜,一个想吃肉食的两位老太太的话,但内中却表现了阶级的对立。这种语言看着平易,而是用尽力气写出来的。杜甫、白居易、陆放翁的诗也有时如此,看来越似乎是信手拈来,越见功夫。写一句剧词,要像写诗那样,千锤百炼。当然,小说中的语言还可以容人去细细揣摸、体会,而舞台上的语言是要立竿见影,发生效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戏剧语言要既俗(通俗易懂)而又富于诗意,才是好语言。
儿童剧的语言也要富于诗意。因为在孩子们的眼里,什么都是诗。一个小瓜子皮放在水杯中,孩子们就会想到船行万里,乘风破浪。我在《宝船》中写到,孩子们不知道“驸马”是什么,因而猜想是“驴”。这是符合儿童心理的。这当中寓有作者的讽刺。如果在清朝末年我这样写,就要挨四十大板。儿童剧要写出孩子们心里的诗意,且含有作家对事物的褒贬。
要多想,创造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