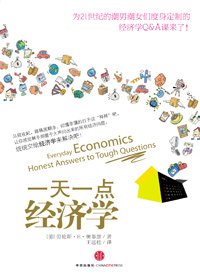破解中国经济之谜-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商四面楚歌,险象环生。2001年下半年,对配股承销商来说,无疑是黑色的日子。由于流通股股东纷纷放弃配股,一些承销商“包销余股”,无可奈何当上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再次,不少私募基金现在已经被套,目前私募基金的保证金已升至50%以上,私募基金在股市里玩的都是资金杠杆效应,这对资金链又是一个考验。面对造假案东窗事发、承销吃不了兜着走、委托理财保底赔付、违规资金清算撤出等四面楚歌,券商资金链随时有可能出现多处断裂。
毋庸讳言,中国证券市场作为世界证券大家庭的一个新生儿,还很稚嫩,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没有充分发挥资源优化配置作用的问题,黑庄操纵股市的问题,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的问题,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问题,上市公司假重组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比较严重,并威胁着国家整体的金融安全。
3。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金融是现代市场体系的核心,而资本市场又在金融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资本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轴心。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大体可以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与资本市场的发育不良相联系的,另一类则主要是由于对资本市场的监管不完善所引起的。
应须看到,目前中国股市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中国股市走过了独特的路,在两个交易所成立之前,深沪市场上已经有了13家上市公司。等到证券法实施和全国监管体制理顺的时候,交易所已经运行近6年时间,并拥有了三四百家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诞生十年后的今天,股票发行方式才开始转向全面市场化,政府的身影才开始逐渐退出。这种先游戏,后有游戏场所、游戏规则和裁判员的历史,造就了市场的不规范。在市场定位上,十年来数次调整。此外,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急急忙忙,十年间走过了国外市场100年的路,快了,就要付出代价。1999年以前的公司都是指标制下上市的。上市指标的计划分配有很大的随意性,捆绑上市很普遍。真真假假,并购、高校概念、科技股、纳米基因等,天花乱坠,请君入瓮。上市之后,逐步出现企业产权不清、应收款无法回收、内部人员控制严重、中介机构没有起到应有的责任、机制转换不彻底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和业绩提升,相当一部分公司已经成为空壳。
中国证监会请来了两位‘洋大人’,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而请来的‘洋顾问’,他(她)们不负众望,仗剑在手,几乎将中国股市翻了个底朝天,到现在,中国人才逐渐明白了股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倒使人们想起了六十年前共产国际给中央红军派来的‘洋顾问’。成败能系于此吗!
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梁定邦在南京大学被聘为客座教授的公开演讲中,展望了中国证券市场未来发展前景。透过梁先生的弦外之音和几分无奈,结合中国股市之怪现象,人们看到了中国股市的几大内在缺陷。缺陷之一,遗留问题难清理;缺陷之二,假帐现象满天飞;缺陷之三,市场设计不合理;缺陷之四,投资价值难衡量;缺陷之五,理性投资欠倡导;缺陷之六,机构投资变投机。这些问题若得不到妥善解决,A股市场将会慢慢地死去。
中国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那么难以琢磨,面对复杂的问题,谁来回天呢!
证监会:两难境地中国的证券监管机关拥有几乎是令各国同行最为羡慕的权力:从证券交易行为,到证券的内部组织;从证券登记到证券服务;从民间裁决到行政处罚。其权力包罗万象,无所不能。作为证券市场的直接监管机构,他每一个决定往往都要造成股价的一次波动。
其实证监会的权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旗下两家证券交易所、1160多家上市公司、1000多家证券经营机构和证券中介服务机构,股市中事无巨细,均可追究到证监会的责任。但证监会的权力缺乏法律基础。关联交易、虚假信息与公司结构及制度上的缺陷有关,证券市场从成立起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仅希望证监会来彻底根治它,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如果急于求成,将会再次背离自然规律或偏离自然力,后果可想而知!
财政部:苦心遥控财政部是国家主管财政收支、财税政策、国有资本金基础工作的宏观调控部门,与证券市场实际上没有直接联系。他通过拟定和执行国有资本金基础管理的方针政策、改革方案、规章制度、管理办法,组织实施国有企业的清产核资、资本金权属界定和登记,负责国有资本金的统计、分析,指导财产评估业务等来影响股市。
而在2001年7·31雪崩前夕,财政部开始大谈国有股“减持”,有关官员对外宣布,2001年到2006年间,社保基金的缺口额度总计4552亿元,本年缺口在600亿元上下。目前填补社保基金缺口的资金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财政超收;二是国有股减持;三是发行彩票等其他途径。而这三个途径主要压力就在国有股减持上,其他两个途径不确定因素太多。明确对外公布国有股的减持压力,等于向全体股民宣布熊市将立刻到来。财政部在很多方面都是在履行自身的职能,有谁又能够说他这样做不应该?
另外,财政部要求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都要按照新会计准则进行财务信息披露,这一要求直接导致许多企业中报预亏预警,直接引发了股市雪崩。也许很多人还把这一笔账记到了财政部的头上,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财政部这样做的“良苦用心”?
人民银行:股市巡警每一次股市暴涨或暴跌,最后的原因无一例外都归结到了银行的头上,理由很简单,证券市场大量的资金从哪里来,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违规资金?而且证券市场的涨落与银行利率天生就是一对矛盾,银行利率高,资金就从股市流到银行;银行利率低,资金也就从银行流到了股市。国外中央银行对股市是宏观调控者,调控手段主要也就是通过调整利率,利率调低,股市高涨;利率调高,股市应声而落。而人民银行对于股市,就如同站在大马路上巡警。查处违规资金,一些庄家成为惊弓之鸟,在调查来临之前先避一避风头。没有人否定违规资金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毒瘤,没有人能够统计到底有多少违规资金在证券市场上运作,但这个巡警的角色也给银行一个两难的选择,违规资金不查处不行,但是一旦查处却引起违规资金逃离股市而造成震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既可以打击违规资金,又不对大盘造成影响?这对银行来说,实在强人所难!
国资部门:股海苦等国资部门的考虑也许更直接一些,一方面中国加入WTO,需要国有资产减持;另一方面,国资部门怎样才能追回每年流失掉的巨额国有资产?可以将国资部门说成一个在海边苦等亲人归来的持灯子女,她对于股市这茫茫大海实际上是无能为力,最多也是举起手中的灯,给在波涛汹涌的股海中的亲人(国有资产)提供一点归航的灯光,但是她期望的国有资产能不能回来,则不是其能够左右得了的。
机构:博弈困境机构应该是中国证券市场最薄弱最不成熟的环节,他对中国股市的作用却也无法替代。为了赚钱老百姓争相追逐机构,一旦被套,“机构”则成为老百姓最为痛恨的对象。“恶庄”、“吸血鬼”成为机构的代名词。股市在较长的时间内,各方的参与者逐渐找到某种适合的生存方式,或者叫“游戏规则”,彼此虽然有矛盾,各自的利益也不同,经历多年磨合后,倒也相安无事。如大多数个人对庄股的青睐,明知其中玄机很多,却难以割舍;而许多机构则扮演庄家角色,既给散户甜头,又深套经验不足的跟庄者;上市公司冷眼观战,一旦市场趋热,或庄家上门寻求帮助,圈钱的冲动则立刻勃发。但在2001年7月29日的股市大雪崩中,人所始料不及的是,机构被套,庄家被困。
股市中的怪现象实际是有意无意中创生的。政府出于想当然的理由,要制定一些政策。比如说规定上市公司3年净资产收益率在10%以上才能增发配股。试想,上市后募集了1个亿的资金,加上原来1个亿,每年必须有2000万的利润才有可能配股,而实际上任何一个好的项目都不可能一两年盈利。那么这个上市公司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做庄炒作,去变通方法,去寻求怪招。它本来过不了这一关,但现自己炒自己,过了这一关,而实实在在的企业反而不敢上市,因为它上市后达不到这个要求。从理论上讲,这个东西不难理解。就像斯蒂格利茨和温斯的信贷配给理论提出,由于存在着“逆向选择”,银行的贷款利率提得越高,老实的企业越不敢来贷款,来的全是骗子和冒险家。由于“逆向选择”,越有能力操纵股市的人越愿意上市,因为它最有“能力”满足监管的要求。可见,政府的垄断、管制本身在创造骗子,然后政府为了防止骗子,设置新的规则,迫使人们更加追求短期行为,进一步吸引创生更多的骗子进来。
资本市场的主要功能是迅速实现资本的流动,降低企业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资本市场的建设,表面上是一种制度和市场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社会利益结构尤其是当代中国中高层利益关系的重组。资本市场的发展将因最初的无序而造就一批‘巨人’(商界精英和优秀企业),这些商界精英和优秀企业,不仅是中国资本市场无序的收益者,还将是资本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直接和主要推进者,这是市场的悲哀,也是市场的精髓。
中国财政的危机有多远?
中国财政收支存在严重的危机隐患。面对严峻的国有企业与银行体系的改革、社会安全体系改革及环境资源的保护等问题,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健全、充裕的财政收支,任何再好的政策构想,也只不过是拔苗助长,无法真正解决问题。
1。中国财政的压力有多大?
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的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从1979年的28。4%下跌到1995年的10。7%,然后稍微上升到1999年14%。这样的比例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32%。特别是,中央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所占的比例更是巨幅下跌。1979年中央政府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6。2%,以后到了1996年只有3。2%,此后微幅上升到1999年的5%。而1999年的比例之所以上升,其中一部分是发行国债所得,政府在未来将面对庞大的债务负担。以这么有限的财政资源,中央政府却必须支付极为庞大的各项改革费用。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的报告,包括医疗、教育、扶贫、年金、基础设施及环境保护在内的极为重要财政支出项目,中国每年至少短缺GDP的4。6%,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总预算的135%。布鲁金斯研究院的经济学者拉迪估计,由国有企业负担的社会福利开销日后必须转移到中央政府的部分高达每年GDP的3。3%,相当于中央政府在1997年的总支出。此外,据世界银行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至少需要投入6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995年整年的GDP。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中国的财政支出中还有相当部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