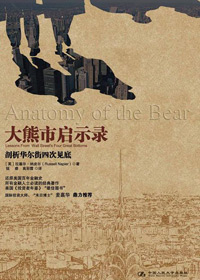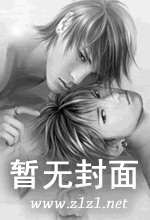大熊猫看小电影-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蒂凡内早餐
龙虾1只,鱼子酱10盎司,香葱1汤匙,黄油15汤匙,鲜奶油5汤匙,鸡蛋6只煎成蛋皮,卷之,索价美金1000大元。这是纽约Le Parker Meridien大饭店在5月中推出的“天价早餐”(Zillion Dollar Frittata)。
Le Parker Meridien里面的这家“诺玛餐厅”,向以“阔佬饭堂”著称于曼哈顿,距第五大道上的Tiffany总部相当不远。基于这一背景,这份早餐的价价格虽是“天价”无疑,却也属事出有因。再说,就鱼子酱的行价而论(以顶级的Beluga为例),每125g(约等于44169盎司)售价三百多美金,“天价早餐”里的那10盎司鱼子酱若是此种品质而又足量的话,不管龙虾和鸡蛋的味道好不好,个人认为马马虎虎似应值回票价。最起码,也算是一份比较货真价实的Tiffany早餐了——奥戴丽赫本藏在牛皮纸袋里的那一份,只有一个丹麦面包,外加咖啡一杯。
当然,材料(公认的)贵重往往只构成“天价”的一个部份,另一个部份,在于毫无道理的“多”。虽然我也曾一手持杓一手持罐一口气吞下过超过10盎司的鱼子酱,虽然把那些鱼子酱升级为Beluga之后此事在我的想象中技术难度应属不高,然而就一份早餐(一人份的!)而言,10盎司鱼子酱实在多余,更遑论那一整只龙虾和6只鸡蛋。事情正如袁枚所说的那样:“尝见某太守宴客,大碗如缸,白煮燕窝四两,丝毫无味,人争夸之。余笑曰,‘我辈来吃燕窝,非来贩燕窝也。’可贩不可吃,虽多奚为﹖若徒夸体面,不如碗中竟放明珠百粒,则价值万金矣。其如吃不得何?”事实上,据“天价早餐”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位顾客事后所发表之感想,“这份鱼子酱足够10个人吃的”。当然,如果Le Parker Meridien不是开在曼哈顿而是哈林区,我愿意毫无保留地收回上述意见。
在报上读到这条消息以后,我就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广州和万水千山之外的Le Parker Meridien的餐厅经理一起翘首以盼着“天价早餐”的第一位顾客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约三个礼拜之后,也就是在消息见报之后第三或第五天的一个上午,悦耳的铃声终于响起在诺玛餐厅,在餐厅其他顾客们热烈的掌声中,一个男人在1只龙虾,6只鸡蛋以及10盎司鱼子酱面前坐了下来……埋单之后他满意地说,味道不错,这样的菜在普通的饭店你根本就找不到。
尘归尘,土归土,凯撒的归凯撒,一切似乎都已很完美了,唯一的遗憾,是这位顾客的身份,他乃英国《镜报》记者安东尼·哈伍德。我因此而怀疑安东尼原来的任务其实是来盯“天价早餐”的首位凯子顾客的。只是因为这位目标顾客的迟迟没有出现,在征求过伦敦总部的意见之后,他老兄于是就幸福地亲自当了一回凯子。当然,按照《镜报》的内部管理政策,这种美差可能只适用于餐厅之类,并且严格限制在1000美金以下,换一个说法,安东尼这次负责“盯”的若是一位在Le Parker Meridien开好了房等待奸夫前来幽会的女名流、并且和房间里的女名流一样苦候不至的话,故事可能就是另一种结局了。
有敢卖的,是因为有敢吃的,吃与被吃,相待如交芦。别说是1000美金一顿的早餐,就算有一个人想吃另一个人,也会有另一个人心甘情愿地被他吃掉。据今年年初开审的德国“吃人案”男主角麦威斯表示,自从3年前他在网上发布启事寻找愿意被他吃掉的人以来,共有6个志愿者前来应征。按照佛家的说法,世间万物互相为缘,皆是因果关系作用下的结果,有一念生,其必因有另一念之起,也就是说,若一个纽约厨师忽一日心血来潮,煎鸡蛋6枚,然后随手抓了一把鱼子酱堆放其上,又碰巧被换班时经过厨房的餐厅经理看到,后者又随手标了个1000美金的价格——这一切表面上的“随意”行为,以因果关系观之其实并不“随意”:其皆因地球上某个地方有某人突然心血来潮地生出了花掉1000美金去吃这样一个“天价早餐”的欲望。
又比如,一觉醒来,你突然(或者是本季度的第九次)冒出一个“今天要是有人无缘无故地送我1000万美金就TMD太好了”的念头,尽管这个念头在三分钟后你扳动抽水马桶的冲水扳手时便告付诸“下”流,然而你仍然需要保持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那绝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妄念。之所以会起此念,是因为彼时彼刻在地球上某一个地方确有一人无缘无故地想把1000万美金送给某人——区别只是在于,纽约的那份“天价早餐”透过媒体的传播终于在伦敦某地找到了远度重洋前来把它吃掉的顾客;透过互联网,德国的吃人狂魔也找到了6个愿意被他吃掉的人,而急于把1000万美金白送给你的那个家伙,迄今为止却仍未能与你取得联络。
我的非典型生活
早上五点,我在网上得知此事。睡前,在卫生间给我老婆留了张字条:“广州流行传染病,原因不明,会死人。少去人多的地方,去买点板蓝根,再买点醋。”
昏睡六、七个小时,被一阵紧接一阵的醋味熏醒。披上衣服下楼,发现我老婆正在用电蒸锅熏醋。她说,超市没醋了,药房里也没板蓝根了。现在熏着的,是厨房里剩下半瓶醋。她还说,真的假的,该不是卖醋的人造谣吧。
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不是谣言。这件事得到了权威单位的证实,并且官式地称那种病为“非典型性肺炎”。报上的发布与网上的说法有多处不同,有些关键问题上甚至相去甚远,不过以下四点都是一致的,即,是传染病;会死人,而且已经有人死了;少去人多的地方;室内熏醋,保持通风;服用板蓝根。
老实说,当时心里真的有点发虚,因为我既没有醋,也没有板蓝根。剩下能做的,只有呆在家里,把窗户门都打开,有点坐以待毙的感觉。夜里,一个热心的深圳朋友打电话来,敦促我赶紧携带家属逃离“疫区”。我严正警告对方不要造谣信谣并且传谣,然后上网去看最新的传闻。
在日夜都开着窗户的家里禁闭了几天,外面的风声好象没那么紧了,于是就上街给自己放风。元宵节之夜,广州的街上出奇地冷清,潮湿的小风里氤氲着暧昧的醋意。真是“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啊。我和一个刚从北京来的哥们坐在酒楼上吃饭,喝酒之前,那哥们先从背囊里掏出几包板蓝根冲剂,当场让服务员用开水冲了,在座者人手一杯,互道保重,然后幸福地碰杯,干了。
回家的路上,接到一个驾车到北京去玩的朋友打来的电话,说正经过湖南,发现这里能买到板蓝根,问我要不要。我说要吧,接下来,他就问我要什么牌子的。
元夕,良辰美景,好端端一个“生查子”之夜,竟沦为“板蓝根”派对。板蓝根上一次大出风头,是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期间。我记得当时上海有传闻说甲肝刚开始流行的时候,上海植物园里的板蓝根,连根带叶,一夜之间全让鸟给倒斥着吃了。
两次传染病流行,板蓝根都义不容辞地充当了超级稳定因素,尽管上一次闹的是肝,这一回闹是肺。“告诉你,照此逻辑——”一位曾亲历上海那次甲肝的酒吧老板盯着我说,“经此广州一疫,我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是满怀希望地憧憬,板兰根可以治疗爱滋病!因为,正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板兰根为什么能既可治肝又能疗肺,所以你我也不可能知道板兰根它为什么就不能治爱滋病。”
我们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一样,都不爱生病,不过我们比较喜欢吃药。而且我们对药物——尤其是中药,向来具有“有病治病,没病防病”之共识。在此次“非典型性肺炎”恐慌中,医生最终是用什么药把患者治愈的,我不太清楚,不过,对于广大市民之“没病防病”,医生自始至终所能提供的可以满足我们对“药”之依恋的药方,除了醋以及把液态的醋加热转化成气态,再就是板蓝根把固态的板蓝根颗粒溶解为液体了。严格来说,醋不能算是药,即使是在一种非典型的情况下,好在我们向有“药食同源”的传统,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所以,醋和板蓝根在市场上一度脱销,实属情有可原,算是“尊医嘱”的一种比较极端的表现。所以,醋就先不去说它,但是板蓝根却是货真价实的药,虽不能当它是救命稻草,要紧的是把根留住。
至于板蓝根为什么能预防“非典型肺炎”,却没有没有权威人士或机构出来说过。而且,这药究竟要怎么个吃法,按何种剂量,都未曾得到过确切的“医嘱”。当然,如果你要求医生把他们开给你吃的每一种药的药理都详尽地解释一遍,他们大概会先建议你转到精神病科看看。再说板蓝根是中药,牛鞭为什么能壮阳?或许成年人都能站在直观的朴素唯物主义立场做出一致的理解,同理,人参为什么益寿,也没有人去问医生。
关于板蓝根,该说的人没说,该知道的人,似乎也不想知道。当然,凡涉及身家性命之事,都不好乱说,也不宜“乱知道”。
直到恐慌已过,才在远离广东的南京某报读到迄今最详细的“医瞩”:“板蓝根对一些上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有一定抗病毒作用,但并不太适用于非典型性肺炎。当然这不是说它没有什幺作用,因为‘喝了总比不喝好’,很多人也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服用的。”“板蓝根本来毒副作用很小,但是用的时间长了,就会积‘药’成疾”。
依然是不得要领。不过说的也是,“喝了总比不喝好”,事实上,我对什幺是“非典型性肺炎”也不太清楚。无论如何,反正我至今仍安全并且典型地活着。回顾我为期一周的非典型生活,唯一想不通的是,为什幺食盐也有人抢购?盐能当药吃吗?近日惊魂甫定,不成想又大吃了一“事后惊”,因为前述想不通之事终于蒙知情人一语道破:盐里面有什幺?有碘。那个病,不是就叫做“非典型性肺炎”幺?
口罩够不够罩
细菌很细,肉眼不可见。相比之下,遮蔽口鼻等等漏洞的口罩就显得巨大无比,不仅显而易见,而且触目惊心——戴还是不戴?近百日来,此事造成的内心煎熬,似已大于疫情本身。
困扰是来自多方面,多学科的。可归类为社会学范畴的有:有病或没有病。在公众场合戴口罩可能被视为传染病患者。因无病戴口罩而遭“公众隔离”的前提条件只有一个:大多数人相信,只有传染病患者才戴口罩。这种共识的潜台词是:大街上戴口罩的人越多,表明患传染病的人越多。“控制”尚未成功,故口罩在“患病”上的像征意义已经超越了其防御性的初衷,个人的“免于恐惧”变质为个人向公众“传播恐惧”。病菌很小,口罩很大,口罩就是放大并且外化了的病菌,至少,口罩“强调”了病菌,正如前巴斯德时代曾有欧洲教会认为便后洗手是一种猥亵行为,因为洗手公开“强调”了如厕的“不洁 ”。若暂不考虑有关法律规定,此种共识之下,一个戴着头盔骑摩托车(或骑单车)的人,一个戴着安全帽进入工地的人,也不是没有机会被视为“头脑有病”或患有某种“思想问题”。
勇敢或怕死——此命题属伦理学范畴。命题

![[火影]最爱大熊猫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5/1591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