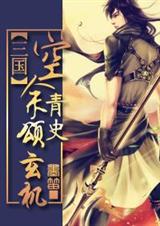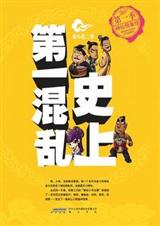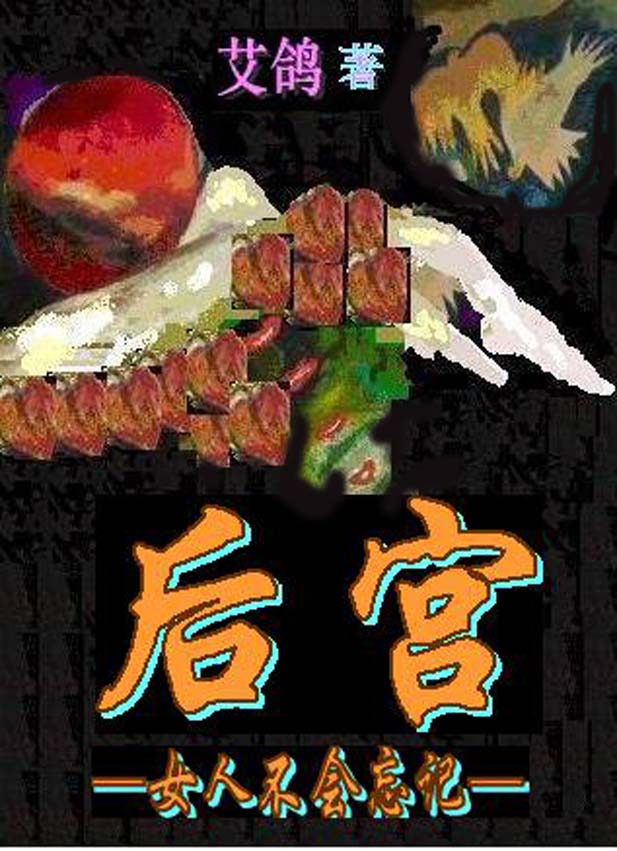中国知青史-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还存在着“三大差别”,这差别,要靠我们去缩小,要靠我们去消灭。要都想离开农村,共产主义咋实现呢?说因为不愿当一名农村家庭妇女,而不愿在农村干一辈子,其根源不在于不愿当农村家庭妇女,而根本问题是有没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的思想,有没有彻底决裂旧观念、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按照她的夸夸其谈,每一位女知识青年都应该心甘情愿地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因为这是“彻底决裂旧观念”的具体表现,缩小“三大差别”的实际行动,而且关系到共产主义能否实现的大目标。事实上,单凭这种将婚姻政治化的说教是无法掩饰问题的真相的,因此也就无助于打消女知青们的疑虑。农村妇女与城市妇女在家庭生活乃至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显著差距,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的一个侧面。它深深植根于现实社会中不同的经济、文化基础上。这种差别,只有在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变革其落后社会关系和陈旧传统观念的过程中,才可能逐步弥合,而绝不是借着一些力量单弱的城市女子与青年农民的结合所能缩小的。大量事实证明:女知青成为农村家庭妇女后,不但没有在改变当地落后面貌方面有所作为,反而为“大有作为”之类的宣传付出了青春和爱情的沉重代价。70年代末,面临知青“返城风”的猛烈冲击,这类婚姻鲜有完好如初者,多数以破裂告终,正应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古话。
。 想看书来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1)
第十一章
政治冤案
“###”中,极左路线猖獗,法制受到践踏,封建专制主义肆虐无忌,冤狱遍及国中。下乡知识青年,处在社会的基层,也难逃其殃。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冤,身陷囹圄;更甚者,因反对极左路线倒行逆施而被处以死刑。关于历史中这最沉重的一页,应从“###”初的“一打三反”运动追溯。
一“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
1970年1月31日,###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认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是:“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求全党:“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2月5日,###中央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根据上述指示和通知,在全国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活动,简称:“一打三反”。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据统计,1970年2—11月的短短10个月间,全国共抓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万名《中国国情总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按照运动的要求,在对“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时,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动员,杀、判之前要交给群众讨论,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立即执行。虽然也提出“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在错误的形势估计和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必然会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1970年8月20日,辽宁的张志新因反对###、“四人帮”,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又遭杀害,是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些下乡知识青年,也在这场恐怖活动中遭到野蛮摧残和无情杀戮。
(一)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大概是“一打三反”运动中惨遭杀戮的第一位知识青年。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内座无虚席,举行10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在一片高昂的口号声中,在10万人高举毛主席语录的红海洋里,19名犯人被推到主席台下听候宣判。其中包括遇罗克。所有男犯人都被剃光头,胸前挂着大牌子。所有宣判词的结语全是一句话:“该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这个阴霾迷漫的日子里,遇罗克为了捍卫真理,壮烈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年仅27岁。
出身的高压、苦难的逆境、历史的责任,把才华横溢的遇罗克的生命化成一团奔突的地火,促使他将批判之剑最先指向极左路线的权威人物。1966年1月,他完成了一篇约3000字的评论《从###的一封信想到的》,借题批判了当时报刊上赫赫一时的“姚文元的机械主义观点”,即姚反对吴晗的《海瑞》,认为历史上无所谓清官。为了驳斥姚文元的谬论,他还写了《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一文寄给《红旗》,却被悄无声息地退回。他不肯罢休,转寄给《文汇报》,于2月13日被摘要发表。后者居心叵测地加了《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这样一个标题,将它作为工人和农民口诛笔伐的“反面教材”。遇罗克未曾畏惧,他在2月15日的日记中充满自信地写道: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2)
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小丑。
在日记中,遇罗克还尖锐批判了“###”爆发前夕全中国急剧升温的现代造神运动。2月6日,他在嘲弄陈伯达一向鼓吹个人崇拜,“亦不可称为高明理论家”之余,反问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在5月3日的日记里他尖锐指出: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有极限,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详见遇罗锦:《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遇罗克对封建主义在中国大陆病态发作所进行的批判是犀利的,他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也是多方面的,代表作当然是那篇惊世骇俗之作——《出身论》。
封建“血统论”的可怕株连,不仅是遇罗克个人的梦魔,而且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看到,1957年反右运动中,错划了大批右派,摧残了许多人才和家庭,并株连他们的子女。至于在农村,地、富家庭出身的男女青年,遭遇更加悲惨。他通过多次社会调查后发现:地富子女,在政治上不能进步、入团,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在人格上低人一等,政治上一有风吹草动就成为批判对象。许多地富子弟,即便体魄健壮、相貌堂堂,也找不到对象,他们连恋爱结婚的权利都没有。地富子弟即使结婚,生下的孩子,也得戴着地富出身的帽子。“四类分子”的子女未尽,再加上“右派分子”的子女,一代复一代,株连的范围越来越广。
遇罗克在“1967年的总结”中这样写道:反动血统论如此猖獗,“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宋文郁等:《他有了真正的金色衣裳——年轻的###主义战士遇罗克纪事》,《中国青年》,1980年8期。。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他在1967年1月正式发表了那篇振聋发聩的力作《出身论》。
《出身论》通篇一万多字,立论严谨,事实充分,语言辛辣,文章阐述了两个大问题:一、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二、重在表现。后一个大问题包括四个小题:1出身和成分完全不同;2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3出身好坏和保险与否毫无关系;4受害问题。文章尖锐指出,封建血统论之所以猖獗一时,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
有些干部所以承认并且推行了这一套反动的政策,在理论上是无知的表现,他们分不清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阶级论,什么是封建地主阶级的门第论;在认识上是###的表现,他们分辨不出青年的哪些表现是本质的,哪些表现是表面的;在工作上是软弱无力的表现,他们不会给青年人提供表现政治思想的机会,他们不会做政治工作,以致把出身当工具,打击一些人,鼓励一些人,以推进工作;在政治上是热情衰退的表现,他们不愿做细致的调查研究,满足于用出身当框框;在革命意志上是怕字当头的表现,他们不敢提拔真正表现好的人,怕负责任。于是这些东西一起推波助澜,形成了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在我们党的身边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现象。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打三反”运动中的冤案(3)
《出身论》一问世,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巨大震动,牵动了千万人的心。它先后重印3次近10万份,每次都一抢而光。各省、市相继出现复制本,抄成大字报贴在街头的形式更为普遍。它是鞭挞封建“血统论”和专制主义的战斗檄文,在千万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因此也就受到极左路线代表者的残酷###。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在一次讲话中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它恶意歪曲党的阶级路线,挑动出身不好的青年向党进攻。”在强大的高压下,《中学###报》被迫停刊。
1968年1月5日,遇罗克锒铛入狱,在监狱里备受折磨。连续不断的审问、戴背铐、关禁闭……都不能使他屈服和抛弃理想。他始终坚信《出身论》的观点是正确的。1970年,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字第30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乾坤特重我头轻——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花城》,1981年4期。。
(二)“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
“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以下简称“共大”)是由13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校毕业不久的学生(其中5名共青团员,3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于1969年11月在银川成立的自学组织。他们最大的26岁,最小的只有21岁,平时就比较注意理论学习,在“共大”成立以前,有人就将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笔记刻印出来,互相传阅。为了进一步交流学习体会,探讨理论问题,成立了“共大”。在“共大守则”中明确提出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地而不是形式地、踏实地而不是虚浮地、勇敢地而不是怯懦地掌握###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强的革命战士”。由于成员不在一地,所以“守则”还规定,“共大”是以“刊物为中心,通过自修与交流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组织成立后,自筹经费刻印过两期“学刊”,刊登了“社论”等6篇文章和3篇农村调查报告。
这些文章和一些书信,有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的体会,也有一些针对极左路线的批判言论。结果在1970年3月招来了一场震惊宁夏全区,涉及北京、湖南的大逮捕。
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是主观主义先入为主,案件没有审查清楚,就轻率地定性为“反革命”,并据此捕人,审讯,找材料;对“共大”的性质及成立的目的没有认真审查,对其成员所写的文章、书信没有认真分析,就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对其成员则片面强调家庭出身,根本没有作全面、历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