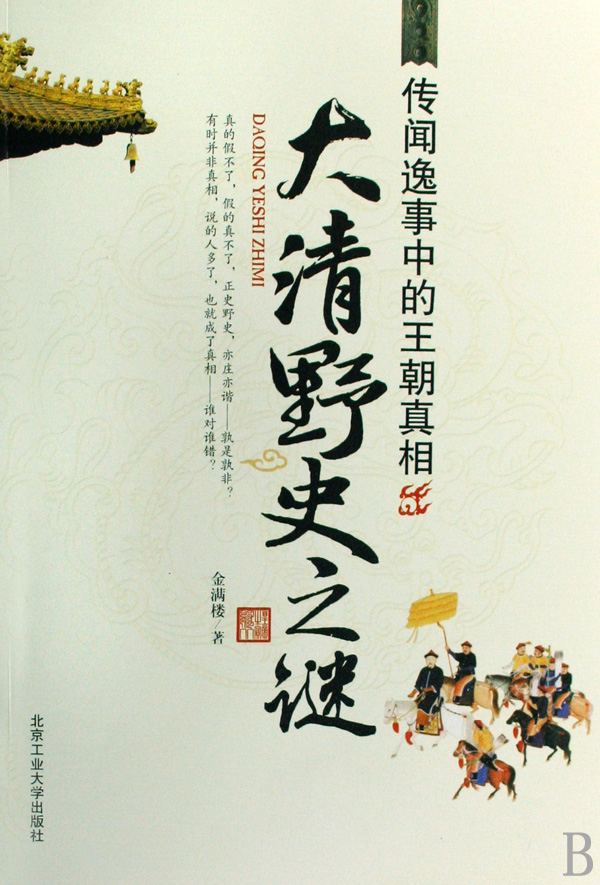清朝三百年艳史演义-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都跟着主人在福建殉难了。我有你老在堂,是不能够死的,还是我去寻香君妹妹入了道吧!你老叫我鬻歌,我看不如鬻琴。女道士鬻琴,卞玉京是做过的,又清净、又高尚,强如奴颜婢膝,去受那北人的糟蹋了。你老也不如同到庵里,免我记挂。”
顿老是无可无不可,听凭孙女作主。香君果然叫他作伴,顿文便改名琴心。
偏仍有那健儿伧父,借着听琴为名,闯入庵里。琴心本已超脱尘滓,不愿带骨粘皮,那知馋猫闻腥,饿鱼见饵,又觉怦然心动起来。顿老原是耐不得静,鬻琴又弄不到几多钱,暗暗叫孙女自寻归宿。香君亦为着清净的地方,任凭俗人来往,未免外观不雅。从前只有郑医生为着卞敏姻事,偶来谈话。如今弄得没有限制,便对琴心道:“姐姐是方外人,鬻琴是风雅的事,玉京师父在日,从不为人轻弹一曲。姐姐怕要学司马相如凤求凰了。”
琴心经不起香君讽刺,依然同了顿老出庵。此时南市、珠市旧院,都是荒烟蔓草,满眼蒿藜,仅有祇陀庵一片干净土而已。香君自琴心去后,觉得岑寂,也以弹琴自遣。至今锦树林二墓,一为玉京,一即香君也。正是:撩乱芳怀归绿绮,模糊绮孽托黄冠。
欲知后事,且听下文。
第六回 马婉容血痕蜚闽峤 柳如是泪渍洒虞山
上回说到顿文为着王子的嫌疑,进了祇陀庵。这时候南京的地方,已经尽力清朝所有。只是附近州县,还有聚众抗命,不肯剃发的。什么宜兴啦,吴江啦,嘉定啦,揭竿斩木,撄城固守。那豫亲王多铎,早已带着刘三妹回京复命了。睿亲王用着汉人杀汉人的政策,命洪承畴经略江南一带,一面却派贝勒博洛顺道入闽。
这班投降清朝的明臣,阮大铖是坠崖死了,马士英是为着通闽斩了,只有苏松巡抚杨龙友,到闽较早,还带着两个妾住着。这两个妾一个叫朱玉耶,一个叫马娇。玉耶原是闽中郭圣仆的宠姬。圣仆在日,最喜收藏书画、瓶砚、几杖这几种玩好。
龙友本来是书画家,得了玉耶,便连古器攫归己有。玉耶对着龙友,情深故主,触目伤心,觉得圣仆的家中较龙友舒适许多。
此时弱草依人,落花误主,忧忧郁郁,不免恹恹的抱病了。龙友最宠的便是这马娇。马娇字叫婉容,原系秦淮的妓女。论他的姿首,濯濯如春月杨柳,滟滟如秋水芙蓉,却当得“娇”这一个字。那知音识曲,妙合宫商,连老妓师都推他独步。婉容说是良家女子,误堕烟花,总要择人而事。龙友在秦淮画舫里,什么卞玉京、郑妥娘、李贞丽这班人,都算仗他帮衬。后来弘光拥立,有了马士英这一个亲戚,居然由清客变做贵人了。马婉容有这班姐妹们的怂恿,居然做了龙友副室。只要杨龙友官运亨通,怕不是顾横波第二吗?不料龙友刚要到苏松巡抚上任,皇帝也走了,宰相也降了。大众为着龙友是士英的党羽,将他的房屋细软,焚掠一空。龙友同玉耶、婉容,只逃得三条性命。知道玉耶闽中尚有一点产业,便悄悄的渡海入闽。正值隆武起用旧臣,龙友自然策名朝列。所有鸾封凤诰,一律都是婉容收受。玉耶心愈不平,又无法夺他的恩爱,阑珊瘦骨,缥缈芳魂,便与郭圣仆到地下作伴去了。
马婉容看得玉耶已死,便要叫龙友将他升为继室。龙友本是善于排场的人,选定吉日,邀集了大学士黄道周、南安伯郑芝龙几个人,替婉容加笄。婉容换了服色,锦裙绣袄,粉黛修肩,与龙友望北谢过帝恩,然后参神谒祖,又拜了黄、郑二人。
龙友已是五十余岁了,婉容不过二十有四,从此鸟鹣鱼鲽,婉容自谓得所。不道龙友的母亲,已经从南京寻到了。婉容见着太夫人,不得不尽点妇道。那太夫人自从丐妇队中,流离琐尾出来的,对着锦衣玉食,自然欢喜无量。看见儿子红袍纱帽,依然是个贵官,也不知道闽中的局面靠得住靠不住。
龙友是日日有朝报的,听得益王朱由本、永宁王朱慈炎,先后窜死,风声渐渐逼紧。黄道周出关募兵,又被洪承畴部将所害。郑芝龙知事不妙,献出仙霞关,已受清朝的侯封了。龙友踌躇无计,想借着护驾为名,跟了隆武暂奔汀州,偏被婉容绊着说:“生则同生,死则同死,老爷殉国,妾身愿殉老爷。
此项时势,逃来逃去,总是一死。死要死得有名,不要像马舅老爷、阮老爷一样死了,还被人唾骂呢!“
龙友被婉容一激,也只好听天由命。外面报:“建宁陷了,清兵已直犯延平。”
又报:“圣驾挈了曾妃,拥了十余簏残书出城了。”
枪声、杀声、哭声、马蹄声,嚷成一片。龙友对着婉容道:“我去死了,你却何如?”
婉容哭道:“如今要烦你先驱狐狸于地下了。”
东南角上起了一片火光,门外便闯进几个北兵,拥着一员裨将,说一声:“搜!”
蜂拥般的进了内室。梁上早挂着一个青衣小帽,修髯盈颊的人。裨将正在问着,北兵早牵了一个白发老妪,一个红粉佳人前来。那老妪只是索索的抖,裨将叫他供的明白。
老妪说:“死的是儿子,后面的是媳妇。”
裨将叫北兵将龙友尸首解下来焚化了,说要借这里房屋住几天,还要叫老妪替他备酒充饥。老妪一句都听不懂,亏得婉容装着和颜悦色的面目,—一答应。
这裨将同婉容七搭八搭的讲说,他是博洛手下的梅勒章京,名叫穆都哩。还把豫王娶刘三妹的事,说给婉容听。婉容吩咐婢仆送上酒肴,亲自把盏。老妪早姗姗的走了。裨将酒落欢肠,把婉容看了又看。婉容凝眸送媚,拨指迎香,还随口唱了一支小曲。裨将解去外面甲衣,只留短袄,要婉容领他到房里去坐。婉容吩咐贴身丫鬟,扶了裨将上楼。只见琴尊妥贴,笔墨精良。裨将是醉翁之意本不在酒,望着婉容从外面进来,便想上前搂抱。说时迟,那时快,裨将腹上,早着了一刀,血流如注,大喊一声,倒在地下。正在挣扎,婉容对着咽喉又是一刀,转手用刀自刎。外面北兵已听着声响。丫鬟更惊得呆若木鸡,定一定神,才向下面报信。北兵进来的时候,老妪带着丫鬟早向外面逃走了。北兵尽掠财物,把房屋付之一炬,连那裨将同婉容的尸首,也在劫数里面了。原来马婉容自从同龙友约定同死,便向家将手里得了这柄倭刀。倭刀锋铦无比,见血即死。却只有闽中同倭国相近,所以常来贩运。婉容杀了这员裨将,从容自殉,要算不负龙友了。后人有诗赞婉容曰:拚将一死证前困,如是横波总贰臣。
莫诩宫中曾刺虎,闽南亦有费宫人。
龙友、婉容有了这个结局,龙友的母亲带着丫鬟,仍旧扮了丐妇,一路打从衢州、严州过了杭州,乘着运河的船到得南京,已是顺治五年四月。龙友的母亲寻着一个故仆,把丫鬟配给了他,在这故仆家中,吃碗现成茶饭。那故仆名叫杨升,新投靠在致仕回籍的礼部侍郎钱谦益门下。丫鬟荐了进去,便派着伏侍柳夫人。柳夫人是侍郎宠爱得很的,名叫如是,亦是秦淮书舫里有数人物。因为侍郎词翰,与己伯仲,才肯归侍侍郎。
侍郎觉得年华老大,恐怕枕席间满不来夫人的意,左一服药,右一服药。倒是夫人说道:“腹中空虚的人,如何比得来饱学,何苦东抄西袭,反被人笑?”
从此,只算做闺房密友,文字挚交。侍郎爱宠中间,又添了几分敬畏。凡有题识,但署“柳君”两字。依附侍郎的,便跟了称做夫人。侍郎本来是提介风雅的,征歌选色,至老不倦。自从得了夫人,一班墨客骚人,都拜倒石榴裙下。这钱侍郎的柳夫人,同龚尚书的顾夫人,真是一时瑜亮。犹记侍郎《金陵杂题》里道:洗粉轻烟佳丽名,开天营建记都城。而令也入烟花部,灯火樊楼似汴京。
一夜红笺许定情,十年南部早知名。旧时小院湘帘下,犹记鹦哥唤客声。
惜别留欢限马蹄,勾栏月白夜乌啼。不知何与汪三事,趣我欢娱伴我归。
别样风流另酒肠,伴他薄幸耐他狂。天公要断烟花种,醉煞瓜洲萧伯梁。
顿老琵琶旧典型,檀槽生涩响零丁。南巡法曲谁人问?
头白周郎掩泪听。
旧曲新诗压教坊,缕衣垂白感湖湘。闲开闰集教孙女,身是前朝郑妥娘。
这都是鼎革后侍郎的寄托。侍郎迎降清朝的时候,原想位登台辅,名动公卿,不料做了几个月的礼部侍郎,依然放归田里。虽然门生故旧,都尊他一声虞山宗伯,但这两朝领袖的名声,终究留着痕迹。因感而愤,因愤而悔,这老境益发蹭蹬了。
幸亏柳夫人借着诗词,替他消消遣,解解闷。侍郎一年一年的窭蹙下来,家用又大,时事又难,从前得过知遇受过恩惠的人,都去捧这班热官,真是“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了。侍郎的儿子,只中了一榜举人,有什么势力,眼睁睁看着老父债台百级,受那乡里豪猾的拨弄,真真没法解救。柳夫人到得这种景况,也知道人亡家破,就在目前。偏是侍郎又为着留宿黄毓祺这一案,被逮江宁质讯。柳夫人又尽出金珠细软,典鬻一空,才保得侍郎老命。侍郎受了这场挫辱,归到虞山,已经奄然一息了。柳夫人自然调汤理药,杨升还四处去筹借款项。不到几日,侍郎料定不能再起,便捏着柳夫人的手,指着儿子道:“他是忠厚无用的读书人。我死以后,这班虎视耽耽的乡里,必定要来同你们为难。我知道你的私蓄也净绝了,我的书画古玩,算不来什么钱,只有这所房屋,还好售卖。你们把我殡殓好了,赶快到南京去躲避。他服满了,仍旧叫他上京应试,继我书香一脉。杨升两夫妇,倒忠心得很,最好跟你们到南京去。”
柳夫人听一句,应一句,泪珠儿湿透了衣袖。等到侍郎怛化,七手八脚的买棺立主,寥寥落落,来了几个吊客。
柳夫人想到昔日繁华,而今何在?倒不如白杨荒草,同穴同埋,也算得此生结果。主意已定,只等着下窆的时间,做个殉葬的姬侍。杨升听见外面沸沸扬扬,说要来索侍郎旧债。夫人叫一家细弱,暂时迁居,此处只剩了侍郎的儿子,同夫人及杨升夫妻四个人。
这日是侍郎的三七,柳夫人上了祭菜,正在呜呜咽咽的哭,只听现门外搪撞诟谇。夫人知事不妙,连叫杨升出外开门。蜂拥着一班少年进来,见了侍郎的儿子,捽住便殴。杨升飞报入内。夫人便缟服练裙,出了中堂,对着少年一望,尽是短襟窄袖,椎埋屠狗的脚色,便指着为首的厉声道:“你等快快放手,侍郎未必尽负汝等金。便是负汝等金,也是侍郎的事,与他儿子什么相干?况且还有我在。你等究竟要多少金呢?”
这班少年听了夫人的话,总道有点沾染,把气焰敛抑了一点,声势和平了一点,只是墙外四面,依然不曾放松些子。夫人便一不做,二不休,连夜刺血写了状子,叫杨升打了墙洞,到常熟县里去告急。静悄悄的乘人不备,用布缕于打了一个结,自缢在侍郎柩侧。到得县中隶役,跟着杨升赶到,少年已是散了一半。敲门进去,见那柳夫人已一瞑不视了。只有侍郎的儿子,同着杨升的妻子,在那里抚尸大恸。县役着实不忍,禀明县官,拿了几个少年去惩办一番,虞山钱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