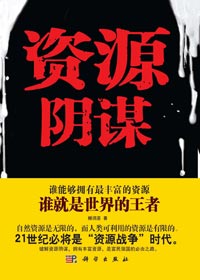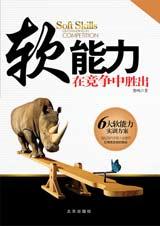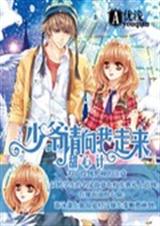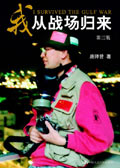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0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建国30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上,军工自成系统。国务院设有国防口,统一归口管理国防工业各个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三机部是航空;四机部是电子;五机部是常规兵器;六机部是舰船;七机部是战略导弹和航天;八机部是战术导弹(在这之前已经撤销)。国防工业口根据军队的要求和军费的安排,给所属各机部下达军工生产任务。
这次改革,就是要拆掉这个口子,打破民用和军用在管理体系上的分离,下属的各个机部和其他民用部门一样,直接归国务院领导,除保留必要的军品生产线外,一律纳入民用系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他不好举这个手。中央确定的事,当然要服从,这是原则。但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毕竟涉及面也太大了。
他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会议还没有散,父亲就打电话给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门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杨尚昆也不清楚。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具体怎么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举一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
其实,军队方面也有误解,打破自成系统的国防工业体系,是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国防工业并不因此而消亡。只不过,从此,军事工业不再是指从事军品生产的企业的总和,而是指所有军品研制和生产活动的总和;军工行业管理的对象不再是原来拥有产权的军工企业,而是与军用有关的技术和生产行为了。
当然,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军工产业内在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后,军队再要什么,那就拿钱订货。过去是按指令办,现在是按合同办。这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的基本内涵。军人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那要花多少钱,人家才同意卖给你呢?飞机大炮难道也能像电冰箱、洗衣机那样在市场上货比三家吗?
既然是向市场化转型,这就必然导致军工产业的企业化改革。
过去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虽然也被称之为军工企业,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既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产品的调拨等都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
这次改革,就是要把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转变为具有独立利益的市场竞争的主体。通俗地说,就是转变为公司。军工部门的企业化改革后,各机部一律改为公司,国家只是出资人,企业享有经营的独立权。传统的行政上下级管理模式和隶属关系将被资本联结纽带关系所替代;集团公司真正以效益为中心,并按照市场导向进行开发经营,逐步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济实体。
这个前景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那么新鲜。当然也有人说,这行吗?是不是有些太邪乎了?
后来听到国务院的几个副总理议论,说又不是断他们的粮,反应这么激烈,真没想到。事情反映到了最高层,稳一稳也好,那就先缓一步吧,邓小平说,分两步走吧,核工业部和航天部暂时不动,其他两个部,兵器和航空先划拉过去。
1984年11月,军委座谈会期间,我和文件起草组的同志们无意中闲聊,谈起这次会议上提到的关于“国防工业自成小天地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大家都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指什么?针对谁?我也很奇怪,是啊!这话是有所指的吗?父亲是主管国防工业的不错,与他有关吗?“小天地”,究竟寓意着什么呢?无论发生什么,都是事出有因。不行,我得问个明白。
晚饭后我陪父亲散步,闲聊中谈起了这件事。
“什么小天地?我怎么不知道?”他说。
咳,文件上都有了!你开会肯定又走神了,又在想你自己那摊子的事,也不听听人家说什么。我责怪父亲,并把文件给他找出来。
他看了后说:“军工体系是历史形成的嘛!又不是谁非要把住。中央决定了拿出去,我们执行就是了。”
在这样一个重大变动的面前,父亲是什么态度呢?应该说,他不是个保守的人,更不是个把事业等同于个人权力和利益的人。但应该承认,这个变化不在他原有思考的范畴之内,也突破了他对国防工业发展的宏观设计。对这样一个全新的概念,对执行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后果,他和他的机关的确需要一个思考和反复论证的过程。
但问题的性质,似乎不完全是工作层面的。小天地!谁在搞小天地了?小天地与独立王国何异?他对这一说法是难以接受的。其实,不就是盯上了国防科技工业这块肥肉了吗?当初,那样困难,求你们,你们不管,说是要我们自己“滚”,现在滚大了,红眼了,就借着改革之名,一锅端了过去。端就端吧,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何必扣帽子呢?
我曾问过父亲这方面的事情,但他的回答很精练简捷:“上面定的。”似乎多一句都懒得说。
但他还是很恭敬地执行了这个决定。
我查到了当时的一份文件。是国防科工委在1984年11月30日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的《关于军工体制改革的原则建议》。内容摘录如下:
张爱萍同志最近邀科工委在京的几位领导同志,研究了如何贯彻执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邓主席、杨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国务院根据当时情况,决定军工自己“滚”……为了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四化建设的大局,军工这支力量,今后应同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的规划,统一安排。据此:
一、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核、航空、兵器、航天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改由国务院统一规划、组织和管理。
……
三、这四个军工部都按照中央的决定,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
……
另外,也可考虑,将核工业部(二机部)、航天工业部(七机部)……同目前一样,仍由国防科工委归口管理。
文件的详细内容就不一一引用了。不难看出,上述的这最后一句,把核工业部和航天部留下,是根据小平同志最后出面摆平时的意见提出的。
父亲于12月26日在这份文件上批示:
赵总理:“杨副主席要我请示你有何指示,以便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对此建议,遵你曾对我指示的原则,我说明如下几点意见。……其另外项,可不必要。虽邓主席提出‘除二、七机部外’。”
不难看出,他的用词极为恭敬,不是批评过他是个“惹不起的人吗”?但他还是挺倔的。我又不是要饭的!要拿就一起拿过去吧,何必遮遮掩掩的,这样倒也干净利落,又不是我个人的财产!
赵紫阳12月27日批示:同意爱萍同志所批各点。
这份报告,可以证明,军工体制改革的决心,以及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是中央最高层决定的。和以往不同的是,本着不争论的原则,事先并没有听取国防工业系统的意见。国防科工委只是根据总的意图,提交了贯彻落实的具体方案。把二、七机部也一并划过去,是父亲最后的意见。
父亲晚年回忆时说:
“80年代初,我遇到的问题是,开始改革开放了,全力发展国民经济。国防工业系统,军工产品需求量减少了,研究、生产部门过剩了,除二、七机部还有事干以外,搞常规武器的力量一下子都闲下来了。整个经济有困难,要靠自己。王震同志是最早提出‘找米下锅’的,试了以后,这个办法不行。我提出,军工企业搞民品,一定要在国务院的统一规划下进行,统一计划、统一安排。但他们那时认识不到这股力量,把国防工业只视为包袱。核电站的那次吵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但两年后,我们自己搞起来了,民品和军贸都起来了,他们这才发现国防科技力量确实有优势。但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一股脑地搬了过去,把这些部门通通转向搞民品,武器装备也不管了。直到现在,也没有把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纳入国家统一规划。
“由于国务院把国防工业的几个部,也搞成了像民用部门那样的经营型性质。这就出现了新的矛盾。例如六机部改成船舶工业总公司后,海军要船,双方就只能讨价还价。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意见,就我国目前的体制和现状看,武器装备不具备采取一般商品的市场经营条件。尤其是战略武器和重大研制项目,只能是国家行为。
“我看到这样的言论,认为国防尖端科技与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现状不协调,是畸形发展。这是不对的,我说是特形。国防科技的领先不是坏事,正是我们的强项。问题在于,应该如何通过国防科技推动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不是限制它、削弱它,甚至是取消它。”
父亲自1956年起,到他1987年退休,在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导岗位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干了30年,实际上是32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步枪到原子弹,从步兵武器到太空武器,伴随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在他晚年,我曾就我国军事科技工业如何面对新的时代的发展这一话题,和他有过无数次交流。其实,在一个新事物面前,许多决策未必一开始就十全十美,许多真知灼见也未必一开始就被认同。中央的态度是“摸着石头过河”,有了问题,改过来就是了。今天,这一切已成往事,父亲当年关于国防工业改革发展的思想,我不忍被时间的长河所湮没,还是记录整理了下来,提供给关心我国国防事业的朋友们。或许多少还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国防工业要不要改革?父亲认为,当然要!但怎么个改法要从国情出发。美国搞的是市场,苏联搞的是计划,我们是沿袭的苏联。在冷战中,苏联垮了,但是不是因此就转而走美国的路?
80年代初,国防科技工业遇到的最大问题,也是最紧迫、最现实的问题,是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的问题;是国家无力支持军工这个庞然大物的问题;是军事科技优势和生产能力没有及时转化为民用的问题。企业转制和市场化是个慢功,市场经济要的是规范、健康的市场,这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国有大型企业的转制,要等待市场的成熟。当时面对的,对国防工业的方针是压缩和转化的问题,而不是拆掉和转制的问题。因此,应该继续坚持调整、整顿的方针,压缩军品规模,在保住军事科技领先地位的同时,发展民品和军贸,走“以军带民、以军促民、以民养军”的我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
1.必须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准备打赢一场战争上。绝对不能为追求近期经济效益而搞短期行为,更不应单纯以减轻政府负担卸财政包袱为目的,简单地把军工科研院所推向市场。
2.坚持以军为主。不管国防工业有没有单独的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