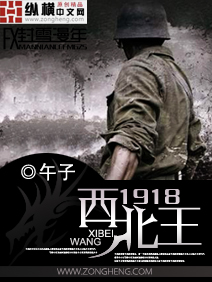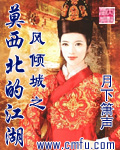西北偏北 男人带刀-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醉,他们都不关心别人的命运。这,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事。
浙江扁头
浙江人在兰州人数之巨,一时无法统计。但有两件事可见出一斑:一是有次过年浙江人包了两架飞机回家;二是兰州有家《鑫报》专门开设了每周八个版的“浙江人专刊”。在兰州,从西到东的主要商业区域都已经被浙江人攻占。兰州人的吃穿用住,不可避免地与浙江人发生了密切关系。
兰州是狭长的河谷地带,南北两山夹着一条奔流向前的黄河,北山高而南山低。有看风水的人说这是“旺客抑主”,就是外地人都如鱼得水,而本地人却有力使不出——“捏住闸了死蹬”。不过,话说回来,在兰州这样一个移民城市,大多数人口其实都是外地人,原生的土著并不很多。浙江人算是兰州的新移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得了一个绰号叫“扁头”。叫此绰号,也并非因为头形果真如此,而是浙江人商业意识浓厚,脑中所想总灵动无比的缘故罢。初时“扁头”似乎还略有贬义,后来也就变得中性起来。当浙江人又开起某一大型商场或小商品批发市场时,总有声音会说:“这些个扁头们确实厉害!”
浙江人季某,只身闯荡西北多年,经营有方,深信做生意和拉网打鱼没什么两样,搞起来一家西服公司,一时间风生水起。用句他们常说的话——“生意不要太好哦!”季某为人处世甚是特立独行,若有地方领导们前来视察工作,他只跟大领导嘈嘈切切,绝不跟二领导眉眼来去。他的脾气弄得领导们很恼火,内部先起了矛盾,彼此都颇有些腹诽,以后的视察真索性全把他避过。他的产品也不请什么形象代言人,所有自家广告全由自己和娇妻担纲出演。我们走在路上,总是不经意间就与广告牌上他那遥远的眼光所对视,身边还有一个女人作小鸟依人状。这种穿衣服的高尚生活方式就这样被他自己在街头巷尾推广开来。儿子出世后,季某在报纸上打出一则通栏广告,宣称“盛世华龙·季”(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已经来到人世,让市民们一下就记住了他未来事业的接班人。
季某在兰州很多年了,几乎成了本地人。很多出走外地的朋友们回来,把酒言欢时,也会随便问上一句:“那个扁头的西装还卖着呢么?兰州也没有啥变化呀!”你看,人们看惯了太多的风云变幻,对一家西服公司的停滞不变都产生了这般感情。我们,似乎都是穿过那个牌子的便宜西装的吧?
早知道黄河的水要干哪(3)
浙江人,在整个中国,都已经成了生意人的化身。很多人没什么文化,但凭着一分一厘日积月累起来的金钱,也成为了人们平庸生活中的传奇化身。
中国最高爱情方式
上学时,他读过这首诗,说的是两个人相爱,他爱了她六十年,她也爱了他六十年,但谁也没有先开口说出那个爱字。一直等了六十年,等到那些曾经相爱的人都已不再相爱,等到那些本来相爱的人开始互相伤害,等到时光摧毁了他们的面容,他和她都已经老态龙钟,老得都快要走不动路了,他才去敲响她的门。大雪落了下来,那是六十年的苍茫大雪……
诗里说,这就是中国最高爱情方式。爱一旦说出,便会失去。诗人告诉大家,心里即使有爱,也先忍着,忍到六十年以后再说,爱还会新鲜如初。在他看来,这全都是些鬼话。新时代里的各种声音都在跳着脚喊:爱要说爱要做爱就要直截了当。爱就爱了做就做了,还哪管什么三七二十一,且顾眼前就是了。他眼下三十啷当岁,离四十岁还差着几年,虽然也是老大不小的年纪,但心态上还年轻。他想,这一辈子若是只爱过一个女人那也是相当苍白单薄的一生。他是画家,是以追求美为己任的艺术家,当然要喜新厌旧。于是,他以一个勾引者的身份出现,向每个自己喜欢的女人大献殷勤,施展各种手段,玩着自己的爱情游戏。每次激情过后,他总感到一阵空虚,质问自己这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爱情。渐渐地,他已分不清爱与非爱的界限,只是凭着一种惯性前行。
他这种在女人之间东奔西突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疾病中断了。偶然的一次感冒发烧住院,竟被诊断出是胰腺上长了恶性肿瘤,是癌症,是呈菜花状生长蔓延之势不可阻挡的癌症。死亡头一次结结实实地砸在他面前,他有些发蒙。从确诊的那天起,他一直恍恍惚惚,忽然对以前曾经全力追求的东西失去了兴趣。开始做化疗以后,他的身体情况变得很糟,头发没几天就落光了,脸色青黑,一副鬼样。疾病开始折磨他,让他甚至都不能回想起从前的欢爱时光。
直到有一天,她,一个他从前的女学生,出现在他的病床前。她的全部神情、话语、气息、泪水、举止甚至因为完全顾不得而生的头皮屑,都表明他的死活对她很重要。她,爱着他,一直都爱,也一直都因他的浮浪之爱而退却。是死亡将她带到了他的床前。她一直都是一个暗恋者,在他看不见的地方受罪。这一次,她却不惜一切地将自己大白于天下,将自己的心思袒露给一向胡作非为无所顾忌的他。时间像鞭子在后面抽打,再不现身出来,什么都来不及了。在病床前,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的起居,甚至不顾他妻子的恶言相向。看起来,只要能让她和他在一起,哪怕只要几天,她就可以承受人世间的一切。
病床内外,其实没有一个人是好受的。他明白了所谓真正的爱,但已无力触摸。一场突如其来的恶疾打开了他生活里全部的秘密,只有死才能解脱秘密的重负,才能解脱爱的苦痛,也才能让他的肉体不再那么一直疼下去。于是,某个清晨,他像一件晾晒的旧衣服一样从六楼窗口跌落下去,谁也没办法再把他从地上捡起来了。
中山铁桥
中山铁桥是“天下黄河第一桥”,来兰州的人总免不了到那儿去留张影。桥栏上有几处被游人磨得光溜溜的地方,是被大众的眼睛安排好的摄影点。
黄河上以前只有一座浮桥,二十四艘大船贯连,浮于河面,冬拆夏设。严冬时黄河结冰,车马都可通行。清光绪三十三(1907)年,清政府在兰州道彭英甲建议和甘肃总督升允的赞助下,动用国库白银三十万六千余两,由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建,美国人满宝本、德国人德罗做技术指导,建起了黄河上第一座铁桥。
老魏的故事离不开中山铁桥的背景。老魏曾经在工厂里做工会干事,业余时间迷上了摄影,还在单位楼梯下的三角间里特地开辟出了暗房。因为照片在一本摄影杂志上发表过,老魏在单位里也算是个文化名人。他为人随和,谁要有个什么事需要拍照,他二话不说背上包就走。摄影的人么,总要跑来跑去的,老不沾家。妻子与他总为此争吵,老魏好脾气,笑笑,认个错,然后一切依旧。在旁人眼里,老魏能干,对家里人也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是个好同志兼好丈夫。
。。
早知道黄河的水要干哪(4)
退休以后,他花白着头发,整日里背着那个看上去很有些年头的尼康相机,手里捏着几张作为样品的相片,在铁桥周围兜揽他的生意。这是他新的职业,就是专为那些到此一游的人拍照留念,然后再把照片按照游客留下的地址给寄出去。老魏的照片拍得中规中矩,虽然在行家眼里算不得水平有多高,但总是能把铁桥相当完整地摄入镜头,让游客咧着嘴笑着和铁桥站在一起。老魏是那些“游击摄影师”里有文化的人,拍照间隙,顺便还介绍一下铁桥历史兼兰州风物。他苍老的面容给人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童叟无欺,拍照生意一来二去的还挺红火。
常在河边走,老魏曾经挽救过几个轻生者的生命。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有个面容悲戚的年轻女人在桥边徘徊了一整天,总是看着滚滚而逝的黄河浊水发呆。老魏觉出有些不对头,就上前搭话。那女人对他所有的问题都摇头不作答,只是不停地往河边走。情急之下,老魏操起手里的相机对着她咔咔连拍,最近处甚至差点把镜头杵到了女人鼻尖。那女人起初竭力躲着镜头,到最后实在忍不住,竟发起火来,破口大骂。骂老魏是花痴,是神经病,是疯子,是流氓。那一刻,老魏反倒呵呵笑了起来。他说:“姑娘,你发火了就不会再想着往河里跳了吧?我知道你心里头有事情,人活着都挺累的,可谁还能比这铁桥更累呢——每天都要有那么多的人和车从它身上过去呢。别想不开,好好活吧!”说着他把相机里的胶卷抽出来扔到了黄河里。据他解释,姑娘家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发愁难看的样子,拍照当时只不过是个劝解的手段罢了,就是为了激一下她。人一生了气就顾不上想死的事了。果不其然,那姑娘被他这么一说,还真的就想开了,事后还找过老魏,也在那铁桥边留了影。老魏手里的样品相册上,就有那姑娘的照片,脸上是笑着的,旁边还有鲜黄的迎春花开着。
老魏总是笑呵呵的,有一张藏得住事的脸。谁都当他是个没有愁苦的乐天派。可谁也看不到老魏心里头也有看不透的黑夜。1989年夏天的一个黄昏,正是可以看到“长河落日圆”的时分,他从铁桥上一头扎进河里,再没浮出水面,只溅起了小小的水花。他的摄影包端正地放在桥边,里面有一封没发走的信,写给一个女人。那女人远在山东,是老魏以前厂里的同事,拒绝了他一辈子。老都老了,越活越没了念想,老魏心里头的那座桥,疲劳过度了,塌掉了。信里头夹着一张照片,背景还是铁桥,是那女人年轻时老魏给拍的。不是单人照,是那女人和一群同事在一起,侧着脸,像在想什么心事。显然,这张照片是老魏偷拍的,悄悄存放了这么多年,安慰着自己孤独的心。
也是在那一年,噩梦般的事情再演:一艘供水船在人工移位时失控,撞在已有82年历史的中山铁桥桥墩上。这艘自重260吨、长米、宽15米的庞然大物,在三根钢丝绳牵引下向北岸移动时,固定在河两岸的钢绳先后全部崩断,船体顺水而下,撞在桥墩上停止漂行。铁桥西边约20米长的人行道严重变形,上面铺设的几十块钢板翘了起来,有的还折叠在一起……
最后一杆
一夜之间,被浙江野木匠大批量制作的粗陋台球桌便撒得满大街都是,让人怀疑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绅士运动”。
绅士不绅士的,且不必说。单从参与进来的各色人等——光膀子的、趿拉拖鞋的、叼烟卷的、带着妞的、吊着鼻涕的、背着书包的——就能知道这已经是一场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了。只打过克郎棋的老同志们形象地把台球叫做克郎球,打球的时候也是把杆子扛在肩头呈半蹲或马步状一眼睁一眼闭然后顺水推舟。一块钱打一盘球,十块钱赌一局球,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群众文化生活。台球室里集合了街上的大小混混,大呼小叫,横眉立目,面容冷峻,直把这里当做了江湖的客栈。
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台球室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江湖,暗地里形成了等级观念,打得好的人成为老大,等而下之就成了跟风的喽啰,会说不会练的就是狗头军师。在这些人的背后,那善使银钱的老板,才是这个小社会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