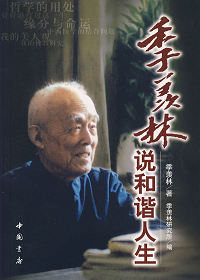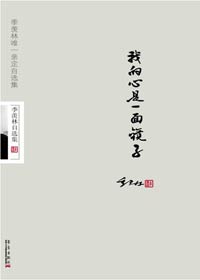季羡林随想录:不完满才是人生-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猪们和猫们有没有天才,我说不出。专就人类而论,什么叫做〃天才〃呢?我曾在一本书里或一篇文章里读到过一个故事。某某数学家,在玄秘深奥的数字和数学符号的大海里游泳,如鱼得水,圆融无碍。别人看不到的问题,他能看到;别人解答不了的方程式之类的东西,他能解答。于是众人称之为〃天才〃。但是,一遇到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的智商还比不了一个小学生。比如猪肉三角三分一斤,五斤猪肉共值多少钱呢?他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因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天才〃即偏才。
在中国文学史或艺术史上,常常有几〃绝〃的说法。最多的是〃三绝〃,指的是诗、书、画三绝。所谓〃绝〃,就是超越常人,用一个现成的词儿,就是〃天才〃。可是,如果仔细分析起来,这个人在几绝中只有一项,或者是两项是真正的〃绝〃,为常人所不能及,其他几绝都是为了凑数凑上去的。因此,所谓〃三绝〃或几绝的〃天才〃,其实也是偏才。
可惜古今中外参透这一点的人极少极少,更多的是自命〃天才〃的人。这样的人老中青都有。他们仿佛是从菩提树下金刚台上走下来的如来佛,开口便昭告天下:〃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这种人最多是在某一方面稍有成就,便自命不凡起来,看不起所有的人,一副〃天才气〃,催人欲呕。这种人在任何团体中都不能团结同仁,有的竟成为害群之马。从前在某个大学中有一位年轻的历史教授,自命〃天才〃,瞧不起别人,说这个人是〃狗蛋〃,那个人是〃狗蛋〃。结果是投桃报李,群众联合起来,把〃狗蛋〃的尊号恭呈给这个人,他自己成了〃狗蛋〃。
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成为社会上不安定的因素。
蒙田在一篇名叫《论自命不凡》的随笔中写道:
对荣誉的另一种追求,是我们对自己的长处评价过高。这是我们对自己怀有的本能的爱,这种爱使我们把自己看得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
我决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应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把它引向自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己而不利人。
我害怕的就是这样的〃天才〃。
第七部分 9。 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一切问题
最近几年,杨武能同志专门从事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卓有成绩。现在又写成了一部《歌德与中国》,真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了。
我个人觉得,这样一本书,无论是对中国读者,还是对德国读者,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它都能起到发聋振聩的作用,一个民族、一个人也一样,了解自己是非常不容易的。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也不例外。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根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世界大势,昏昏然,懵懵然,盲目狂妄自大,以王朝大国自居,夜郎之君、井底之蛙,不过如此。现在读一读当时中国皇帝写给欧洲一些国家的君主的所谓诏书,那种口吻,那种气派,真令人啼笑皆非又不禁脸上发烧,心里发抖。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统治者,在殖民主义者面前,节节败退,碰得头破血流,中国人最重视的所谓〃面子〃,丢得一干二净。他们于是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一变而向〃洋鬼子〃低首下心,奴颜婢膝,甚至摇尾乞怜。上行下效,老百姓也受了影响,流风所及,至今尚余音袅袅,不绝如缕。鲁迅先生发出了〃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的慨叹,良有以也。
怎样来改变这种情况呢?端在启蒙。应该让中国人民从上到下都能真正了解自己,了解历史,了解世界大势,真正了解我们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看待一切问题,都要有历史眼光。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不总是像解放前一百来年那个样子的。我个人认为,鸦片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西方人看待中国同那以后是根本不同的。在那以前,西方人认为中国是智慧之国,文化之邦,中国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令人神往的。从17、18世纪欧洲一些伟大的哲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从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的著作中,也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点。杨武能同志在本书中详尽地介绍了这种情况。
这充分告诉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看待自己要有全面观点、历史观点、辩证观点。盲目自大,为我们所不取。盲目地妄自菲薄,也绝不是正当的。我们今天讲开放,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们对西方的东西应该有鉴别的能力,应该能够分清玉石与土块、鲜花与莠草,不能一时冲动,大喊什么〃全盘西化〃,认为西方什么东西都是好的。西方有好东西,我们必须学习。但是,一切闪光的东西不都是金子。难道西方所有的东西,包括可口可乐、牛仔裤之类,都是好得不能再好、不可须臾离开的东西吗?过去流行一时的喇叭裤现在到哪里去了呢?我们今天的所思、所感、所做、所为应该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在若干年以后,回头再看今天觉得滑稽可笑。我在这里大胆地说出一个预言:到了2050年我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回顾今天,一定会觉得今天有一些措施不够慎重,是在一时冲动之下采取的。我自己当然活不到2050年,但愿我的预言不会实现。
这一本书对德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读者怎样呢?我认为也同样能起发聋振聩的作用。有一些德国人——不是全体——看待旧中国,难免有意无意地戴上殖民主义的眼镜。总觉得中国落后,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好像是中国一向如此,而且将来也永远如此。现在看一看他们最伟大的诗人是怎样对待中国的,怎样对待中国文化和文学艺术的,会促使他们反思,从而学会用历史眼光看待中国,看待一切。这样就能大大地增强中德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这一点是可以断言的。
基于上面的看法,我说,杨武能同志这一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难道不是这样吗?是为序。
(本文是为《歌德与中国》写的序言)
第八部分 1。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
中餐与西餐是世界两大菜系。从表面上来看,完全不同。实际上,前者之所以异于后者几希。前者是把肉、鱼、鸡、鸭等与蔬菜合烹,而后者则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大多数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菜好吃,那么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肉菜合烹呢?这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都用不着。可他们就是不这样干。文化交流,盖亦难矣。
然而,这中间还有更深一层的理由。
到了今天,烹制西餐,在西方已经机械化、数学化。连煮一个鸡蛋,都要手握钟表,计算几分几秒。做菜,则必须按照食谱,用水若干,盐几克,油几克,其他作料几克,仍然是按钟点计算,一丝不苟。这同西方的基本的思维模式,分析的思维模式,紧密相连的。我所说的〃哲学的高度〃,指的就是这种现象。
而在中国,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菜系繁多,据说有八大菜系或者更多的菜系。每个系的基本规律是完全相同,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蔬菜与肉、鱼、鸡、鸭等等合烹。但是烹出来的结果则不尽相同。鲁菜以咸胜,川菜以辣胜,粤菜以生猛胜,苏沪菜以甜淡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于此道并非内行里手,说不出多少名堂。至于烹调方式,则更是名目繁多,什么炒、煎、炸、蒸、煮、氽、烩等等,还有更细微幽深的,可惜我的知识和智慧有限,就只能说这样多了。我从来没见哪一个掌勺儿的大师傅手持钟表,眼观食谱,按照多少克添油加醋。他面前只摆着一些油、盐、酱、醋、味精等作料。只见他这个碗里舀一点,那个碟里舀一点,然后用铲子在锅里翻炒,运斤成风,迅速熟练,最后在一团瞬间的火焰中,一盘佳肴就完成了。据说多炒一铲则太老,少炒一铲则太嫩,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谁也说不出一个道道来。老外观之,目瞪口呆,莫名其妙。其中也有哲学。这是东方基本思维模式,综合的思维模式在起作用。有〃科学〃头脑的人,也许认为这有点模糊。然而,妙就妙在模糊,最新的科学告诉我们,模糊无所不在。
听说,若干年前,一位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的夫人,把《随园食谱》译成了英文,也按照西方办法,把《食谱》机械化,数学化了,也加上了几克等等。有好事者遵照食谱,烹制佳肴。然而结果呢?炒出来的菜实在难以下咽,谁都不想吃。追究原因,有可能是袁子才英雄欺人,在《食谱》中故弄玄虚;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这位夫人去国日久,忘记了中国哲学的精粹,上了西方思维模式的当,上了西方哲学的当。
第八部分 2。我的怀旧观
《怀旧集》这个书名我曾经想用过,这就是现在已经出版了的《万泉集》。因为集中的文章怀念旧人者颇多。我记忆的丝缕又挂到了一些已经逝世的师友身上,感触极多。我因此想到了《昭明文选》中潘安仁的《怀旧赋》中的文句:〃霄展转而不寐,骤长叹以达晨;独郁结其谁语,聊缀思于斯文。〃我把那一个集子定名为《怀旧集》。但是,原来应允出版的出版社提出了异议:〃怀旧〃这个词儿太沉闷,太不响亮,会影响书的销路,劝我改一改。我那时候出书还不能像现在这样到处开绿灯。我出书心切,连忙巴结出版社,立即遵命改名,由《怀旧》改为《万泉》。然而出版社并不赏脸,最终还是把稿子退回,一甩了之。
这一段公案应该说是并不怎样愉快。好在我的《万泉集》换了一个出版社出版了,社会反应还并不坏。我慢慢地就把这一件事忘记了。
最近,出我意料之外,北大出版社的老友张文定先生一天忽然对我说:〃你最近写的几篇悼念或者怀念旧人的文章,情真意切,很能感动人,能否收集在一起,专门出一个集子?〃他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悼念胡乔木同志的文章。他这个建议过去我没有敢想过,然而实获我心。我首先表示同意,立即又想到:《怀旧集》这个名字可以复活了,岂不大可喜哉!
怀旧是一种什么情绪,或感情,或心理状态呢?我还没有读到过古今中外任何学人给它下的定义。恐怕这个定义是非常难下的。根据我个人的想法,古往今来,天底下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和动植物,总在不停地变化着,总在前进着。既然前进,留在后面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会变成旧的,怀念这样的人或物,或人生的一个阶段,就是怀旧。人类有一个缺点或优点,常常觉得过去的好,旧的好,古代好,觉得当时天比现在要明朗,太阳比现在要光辉,花草树木比现在要翠绿,总之,一切比现在都要好,于是就怀,就〃发思古之幽情〃,这就是怀旧。
但是,根据常识,也并不是一切旧人、旧物都值得怀。有的旧人,有的旧事,就并不值得去怀。有时一想到,简直就令人作呕,弃之不暇,哪里还能怀呢?也并不是每一次怀人或者怀事都能写成文章。感情过分地激动,过分悲哀,一想到,心里就会流血,到了此时,文章无论如何是写不出来的。这个道理并不难懂,每个人一想就会明白的。
同绝大多数的人一样,我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人。人的七情六欲,我一应俱全。尽管我有不少的缺点,也做过一些错事;但是,我从来没有故意伤害别人;如有必要,我还伸出将伯之手。因此